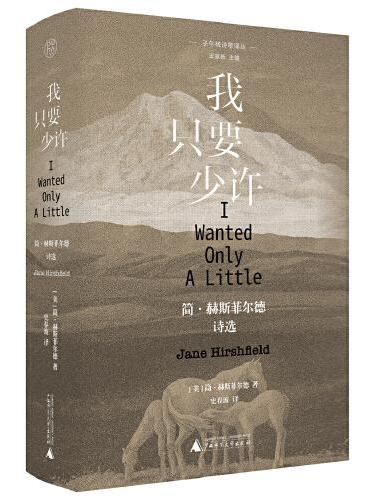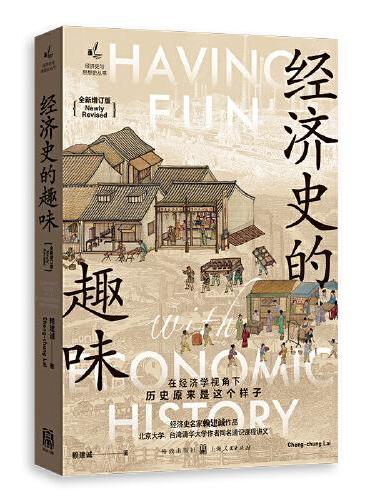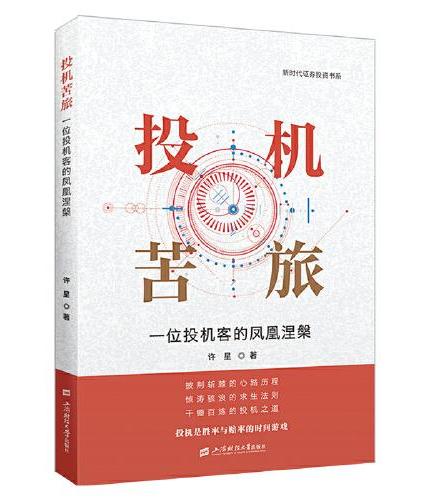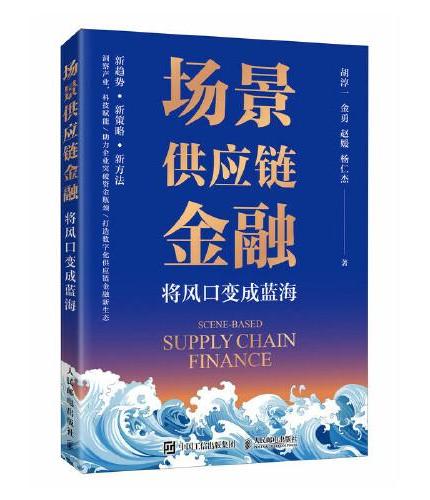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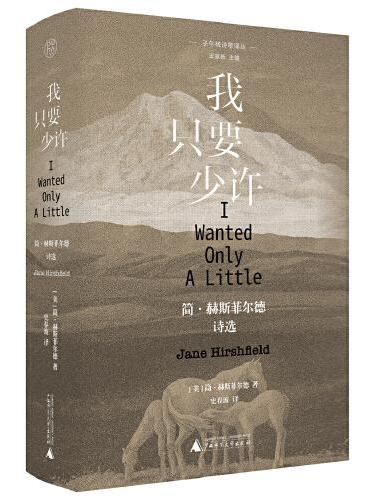
《
纯粹·我只要少许
》
售價:HK$
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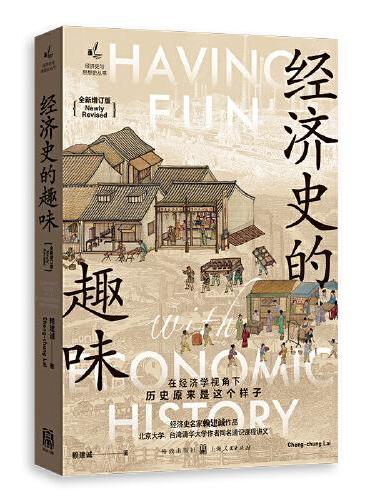
《
经济史的趣味(全新增订版)(经济史与思想史丛书)
》
售價:HK$
84.0

《
中国古代鬼神录
》
售價:HK$
1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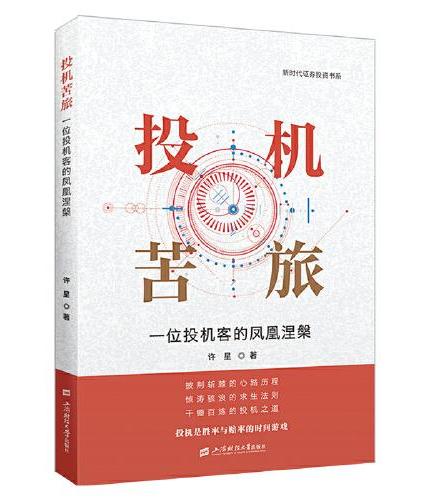
《
投机苦旅:一位投机客的凤凰涅槃
》
售價:HK$
88.5

《
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
》
售價:HK$
69.4

《
日子慢慢向前,事事慢慢如愿
》
售價:HK$
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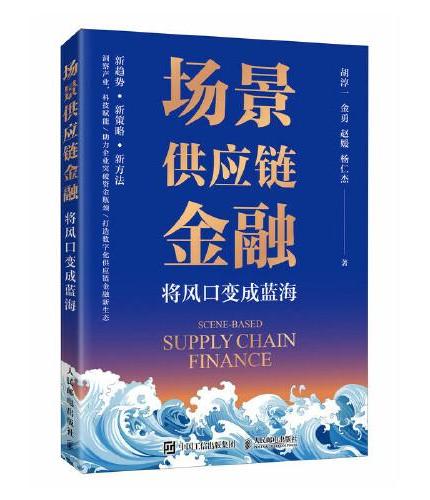
《
场景供应链金融:将风口变成蓝海
》
售價:HK$
111.8

《
汗青堂丛书146·布鲁克王朝:一个英国家族在东南亚的百年统治
》
售價:HK$
91.8
|
| 編輯推薦: |
周嘉宁作品
凝聚十年的成长印记
轻触微蓝的青春
一腔怅惘也化作了流年
不要哭,我会研磨了光阴来陪你
|
| 內容簡介: |
此文稿为周嘉宁的中短篇作品集,该作者出自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现任《鲤》杂志文字总监,其文风格清新自然,近几年文字更是越发成熟,此次作品集,也是对于她个人作品成长的一个记录。
文字:
这时候,电影院的霓虹灯暗下来了。
那最后走出来的人,竟然是保罗先生,还有一个女人。我隔着玻璃注视着他们,他们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然后保罗先生撑开一把黑色的大伞,把那个过分娇小的女人彻底笼在了伞下来,他们靠得很近,保罗先生一定搂着她。他们朝咖啡馆走过来,我也不知为何竟然紧张得,几乎要窒息。但是保罗先生并没有进来,或许是因为今天咖啡馆的热闹程度出乎了他的想象,过去他从未在这个点进咖啡馆,这个点的时候,他已经坐在了他的火车座里面,他已经浸泡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他大概被这热闹吓坏了,朝女人微微一笑,就牵着她的手走过去了。我缩在一堆坐在吧台上喝酒的客人们身后,竟然唯恐被他看到,唯恐他看到我,一个人,擦着擦也擦不完的碟子,永远都是这样,永远。
最后我瞥到一眼那个在伞下的女人,她穿着双夹脚的拖鞋,皮肤黝黑,有只肥硕的屁股,眼神不定,头发油腻腻地披在肩膀上,像是那种在菜场和洗头店里常常能够看见的女人,总之一无是处,完全又将是保罗先生日后给别人留下的一个笑柄。但是保罗先生就是会把这样一个女人搂在身边,毫无审美,满怀柔情。
这个女人会看他写的小说么,会在知道他只是个贫困潦倒,被困中国的作家以后,就抛弃了他么?我在等着这一天么,等着他被抛弃的这一天,再次回到咖啡馆来,露露再往他的意大利特浓里吐一口唾沫,我为自己的恶毒而颤抖起来。直到打烊雨都未停,我在瓢泼大雨中骑着自行车经过那些桥洞,我觉得自己真的正在变成电影里面的,终结者二代,冷酷,无情。
|
| 關於作者: |
周嘉宁,1982年生于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
著有长篇小说《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女妖的眼睛》《夏天在倒塌》《往南方岁月去》等,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情人》《撒谎精的时光宝盒》等,另有译著《写在身体上》。
|
| 目錄:
|
苹果玛台风
一九九三年的火烧云
小绿之死
阳春三月
裸身国王
超级玛里奥在哭泣
明天大厦在倒塌
游泳池
|
| 內容試閱:
|
苹果玛台风
苹果玛台风来的那天是有预报的,预报说苹果玛台风从南面吹往北面,再从北面吹往北面的北面。我有点激动,因为苹果玛台风来了,我似乎是在等它,而且似乎等了它很久。在此之前我敲光了屋子里所有的玻璃窗,我住在二十九层,从来不担心有人会从窗户外面爬进来,而且可以光着身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或者是不整理房间把吃完的泡面碗扔得到处都是,它们发霉,长出小虫子飞来飞去。只是风很大,洗完澡坐在房间中央的时候风总是让我的头发散得像蓬杂草,而且身上的水珠子一旦蒸发我就簌簌发抖起来。我扔掉了房间里所有轻便的东西,剩下的只是几只沉重的装满东西的大柜子和一个收音机。
我没有别的意思,敲光了所有的玻璃窗,只是因为这样使我可以比其他任何人都预先知道苹果玛的到来,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从六月底到整个七月,风一直没有任何的异样,这里的风就是这样的,带着沿海城市的咸湿,吹在脸上让你觉得湿润的窒息接着却是嘴唇和头发里干枯的感觉。我每天都在等待着风的变化,可是这很难,我到底还是不知道台风是怎么回事情,只记得会下雨会下很大很大的雨,并且马路边上巨大的梧桐树会被吹得从根部开始断裂,但是它们并不是轰隆隆地一下子倒下来的,它们往往发出咯吱咯吱的断裂声,然后才犹豫着向着某一个方向缓慢地倾斜,所以我从来不担心会被树砸到。也会有积水,积水会很多,多到走在马路上看不到自己的小腿,是浑浊的。
关于台风,其他我还知道多少呢。
甚至它们的名字,我都讲不清楚,它们总是有着出乎意料的名字,念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卷舌头,有时候需要用牙齿把舌头咬住,苹果玛,我并不知道它会叫苹果玛,但是我还是坐在屋子的中间簌簌发抖地等待着它的到来。
我发誓这种等待并没有想象中的无聊,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几点,可是天很快就会暗了,我就坐在没有玻璃的窗户边上抽烟,在点燃打火机的时候火苗会被风吹得乱窜,我必须左右晃动着脑袋,然后只有三根烟的工夫天就会暗掉。接着就是风,整个房间里面都是风,它们充满了所有的空间把我狠狠狠狠地压缩着,甚至会感到疼,感到骨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再往后,风就可以穿透我了,我总是耐心等待这样的时刻的到来,充满希望,等待它们能够在狠狠地挤压我以后穿透我,从我的手指穿梭到我的尾骨,从我的眼睛穿梭到我的膝盖,从我的肘部穿梭到我的脚底,它们全无章法,满是惊喜。
而且我还有一只收音机,是一只熊猫牌的国产收音机,可是天线确实灵敏,可以收到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声音,这次是口琴,口琴像根细细的弦一样在我的心脏上面慢慢地勒紧,时重时轻不可预测,天空中的玫瑰红尤其鲜艳,混杂在黑暗里依然熠熠生辉,我不知所措地坐在房间中央听着口琴和收音机里沙沙的杂音,身体僵硬无法动弹。
后来我才开始想我为什么在等待苹果玛的到来。
于是我想到了张五,是的,因为我想打电话给他。
为什么现在不能够打电话给他?
因为房间里没有电话机。
可是楼下有投币的电话机,扔一个一块钱的硬币下去就可以听到嘟嘟的声音。
那就是因为没有台风,我要打电话给张五告诉他台风来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先告诉他。
为什么?
让我想想,我说出来你要相信,因为张五想在刮台风的晚上坐在二十九楼的楼顶抽一根黄壳子六块五毛钱的骆驼,就只抽一根,所以我在等待,他们说我在等待的是张五,不,他们都在往哪里想啊,他们是谁,他们干嘛要管我和张五的事情。
张五要在一个刮台风的晚上坐在二十九楼的楼顶抽一根烟,我只是想在第一时间告诉他要刮台风了,快点去楼底下的胭脂店里去买六块五毛钱的黄壳子骆驼,我没有别的意思,这是真的,真的。
整个七月一直就很热,连风都是温润的,我终于不再簌簌发抖,事实上我接了一根水管子到房间里面,这样在闷热得无法喘气的时候我可以往身上浇带着温度的凉水。我开始变得紧张,非常非常地紧张,因为往常的七月总是台风开始出没的月份,而闷热的天气却让我的神经变得异常的迟钝,我不再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风穿透我身体时的运动,不能够确切地说出来风是从哪里穿梭到哪里,所以我紧张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子,用鼻子嗅着空气里咸湿的味道,常常有一丝的异常但是转瞬即逝,我无法捕捉,浑身是汗。
只有在凌晨的时候会稍微好一点,温度微微下降,我则空睁着眼睛坐在黑暗里面一动不敢动地感觉风的变化,风的变化是这样的,有时候它们能够令我左手手臂上起鸡皮疙瘩,有时候我右边小腿上细小的汗毛会倏地一下立起来,有时候我口干舌燥,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在努力地调动着身上所有的感觉细胞,我想我的神经末稍一定都努力地挣扎着它们的小爪子,要知道我是多么地筋疲力尽了。可是我知道它离我近了,它从大西洋或是太平洋或是黄海或是渤海或是其他任何任何地方缓慢地接近我,我焦灼不安。
要知道,我真的是多么多么地筋疲力尽了。
于是我所能够做的就是乱想,我能够想象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台风来了,我是如何地把一条长长的宽松的白裙子从头顶套进身体,撑起一把伞急匆匆地跑下楼去,可能还没有下雨,但是风已经变得很大,大得足够可以把我的伞吹成一朵开起来的大波斯菊,我就举着大波斯菊站在楼底下的公用电话亭里,扔进一个一块钱的硬币,听到话筒里嘟嘟的声音,我要说些什么,我说张五啊,我是四四,要刮台风了。
他会说什么呢,我无从知晓。
他是不是还记得四四,或者他是不是还记得他对四四说过的话。
可是这个情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到后来每一个细节都是烂熟于心的,包括裙子套过头顶时鼻子里闻到的洗衣粉的味道,伞的颜色,那应该是一把银红颜色的三折伞,断掉了一根钢丝,一块钱在我手里面捏出来的温度,公用电话亭子的颜色是透明的黄绿颜色,电话按键上面的数字零已经残破掉了,可是按上去还是有声音,因为张五家的电话号码里有三个零,我按了,而且确实接通了,可是接通以后,就是空白了。
再后来我们确实坐在了屋顶上面,不是张五一个人,而是我们。
我们坐在屋顶上面,雨水哗啦啦地在平坦的二十九楼屋顶反复流动,发出急促的声音四处寻找着出口,我还是撑着我的大波斯菊,当然它已经没有用了,断了三根或者四根钢丝,但是我喜欢就这样撑着它,我的头发和张五的头发就紧紧地贴着我们的额头,所有的东西都紧紧地贴着我们的身体,我们中间是间隔一米的台风和雨水,我在抽烟,而张五一直在弄他的打火机,发出喀哒喀哒的声音,反复如此,他无法把烟点燃,他尝试了各种姿势都没有办法点燃他手里的黄壳子骆驼。
张五说了一句,狗日的。
我们的面前是低矮的灰朦朦的楼房,这里是低矮的灰朦朦的楼房,那里还是低矮的灰朦朦的楼房,到处都是低矮的灰朦朦的楼房。
我开始在屋子里面挂一些纸片,大部分时间我只是把纸片撕成条条贴到天花板上垂下来,高兴的时候我也会做几架纸飞机悬在半空中,我的房间里面有了很多的纸片和三架纸飞机,在整个七月里我高兴过三次,一次是因为天气突然变得异常闷热,我从二十九楼的窗户往下看,看到很底下很底下有密密麻麻纠集在一起的蜻蜓,我甚至听到它们翅膀震动的声音,还有两次,我忘了。那些纸片让我知道今天风是从左面吹往右面,明天风又是从右面吹往左面,今天风很大,纸片在天花板上发出簌簌的惊人响亮的声音,明天风更加大,三十三片纸片从天花板上面落了下来。
这有用吗,我不知道,我连即将到来的台风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在等待的就是苹果玛,在大气层里有多少台风在酝酿,我无从知晓,每天的天空都如往常一样地微微泛着玫瑰红,我想快了,七月都快到头了。
睡眠被我驱逐了,每时每刻台风都有可能会来,它总是充满惊喜,不用敲我的玻璃窗就可以径直钻进我的屋子,我干枯地坐在房间的中间,什么都不干,神经末梢紧紧地抓着周围每一丝游离过去的空气,呼吸紧张,天空就是暗了又亮亮了又暗,我喜欢清晨的风,它咸湿地温柔地钻进来带着我无比想念的凉意,从我的鼻孔穿梭到我的手指尖,这让我完全干枯的眼睛又重新微微湿润起来,而傍晚的风则是暖烘烘地从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渗透进去,在身体里像条河那样缓慢地流动,不动声色地蒸腾着热气,其他时候的风我无法形容,因为它时刻都在变化,我的语言跟我的身体一样苍白干枯得可怕。
我充满喜悦,因为我感受到它的临近。
它们把窗框震得发出轰隆隆哐的声音,它就在它们之中,它混迹其中不可辨认,可是我知道它要来了。
晚上,我把收音机调来调去,我又再次搜寻到我喜欢的声音,我总是可以搜寻到我喜欢的声音,那天晚上我甚至听到了在伦敦上演的一幕歌剧,伦敦是在哪里我一无所知就好象我不知道台风会在哪一天来一样,可是那天晚上我确实就是这样安静地坐在房间的中央,安静地听着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是个女人在唱,我猜想她是个肥硕的女人,因为她的声音就好像是从一个巨大的音箱里传出来一样地空旷,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可是一闪而过,那天风真的很大,我安静地盘腿坐在房间中央听着女人的声音,无线电波干扰发出沙沙的杂音,我有点困惑,有点难过,那个女人的声音慢慢地往上攀爬,风就从我的脚底穿梭到我的头盖骨,它们在那里盘桓了一会儿就砰地冲了出去,它们再次穿透了我。
直到早晨,我的脸早就已经被风吹得如同地上被我踩烂的纸片,我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裂开了一道口子我舔到了甜丝丝的干了的血块。
风正面吹过来我的头发全部往后面扬起来,我闭上眼睛。
这里是九九九兆赫每天早晨六点播送的天气预报:今天凌晨苹果玛台风将影响本市,它从南面沿海向本市靠近,估计在苹果玛台风的影响下,本市将出现降雨天气,雨量大到暴雨,台风天气将持续两到三天,然后苹果玛台风向北面转移。请有关部门做好准备,请张五同志立刻到楼底胭脂店去买黄壳子的骆驼。下面是其他地区的天气情况……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我一直忘记有天气预报的存在,那些指针和仪器一定比我早感觉到它的到来,它的名字叫苹果玛,你看,他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这真的是个令我伤感的名字,我难过异常,因为我终于还是没有成为那个第一个告诉张五刮台风的人,收音机里的女人有多么悦耳的声音,说话不急不缓,每分钟说的字数总是定数,可是她怎么会知道张五想在一个刮着台风的晚上爬到二十九楼的屋顶上去抽黄骆驼呢,张五对她说了吗,张五对多少人说过,又有多少人记得。
反正我是记住了,我活该。
我把身体慢慢地蜷缩起来,又开始簌簌发抖,要刮台风了,可是我没有玻璃窗。
我不想管这些了,我要睡觉了,我太久没好好睡上一觉了。
我们坐在屋顶上,不是张五一个人,而是我们,我们坐在屋顶上,是一个小平房的屋顶,有小阁楼和瓦片,我们都没有穿鞋子,太阳很好,张五穿着沙滩短裤和背心,我穿着白颜色的宽松长裙子,太阳真的很好,而且一丝风都没有,张五的手里拽着一包捏皱的黄壳子骆驼,里面还剩下三根,他嘴巴里叼着一根,吸了一半,还有一半,我问他要了一根,他说女孩子抽烟老得快,但是还是给了我,我用一个粉红色的打火机去点,可是点不燃,无论我用怎么样的姿势都点不燃,打火机发出喀哒喀哒的声音,我多么熟悉这种声音。
我对张五说,张五,要刮台风了。
张五抬抬头看看太阳,晃晃脑袋说,狗日的,那么热,刮台风就好了。
我说,真要刮台风了,这是真的。
张五说,哦,好,这是真的。
没有一丝风,我们纹丝不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