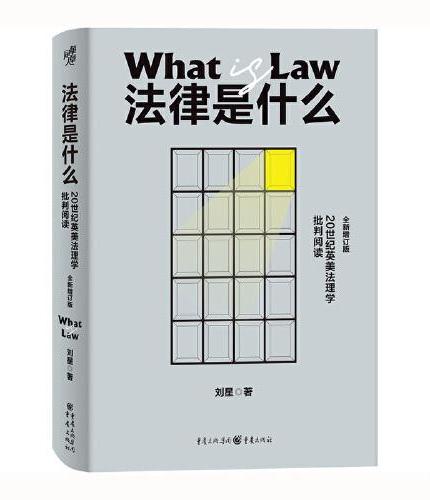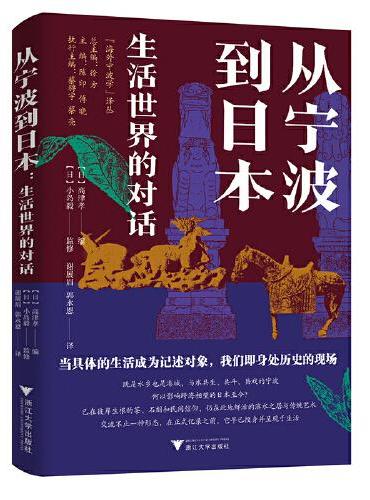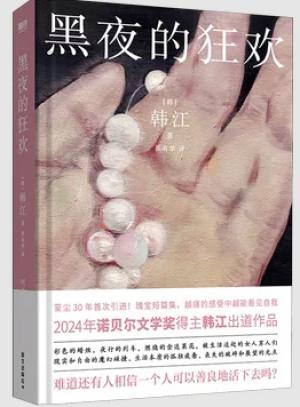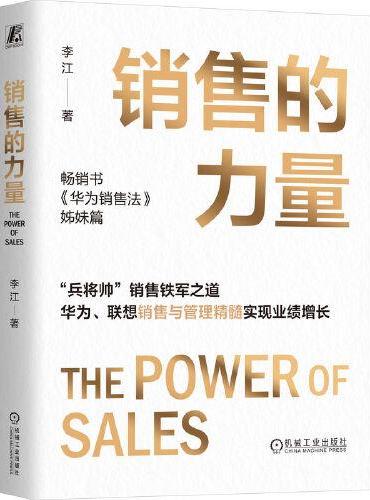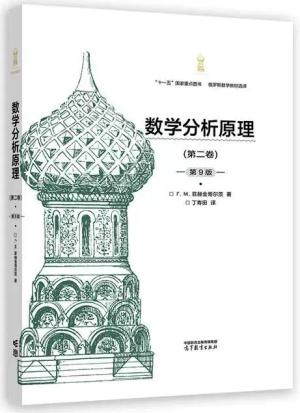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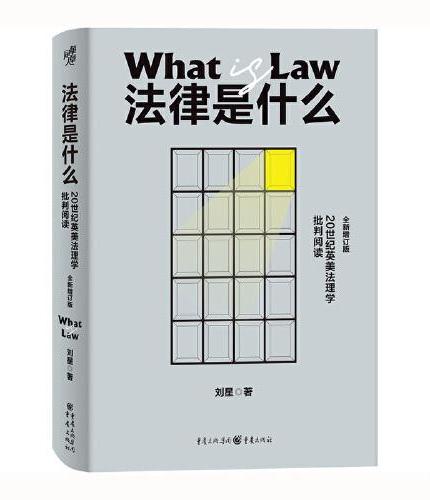
《
法律是什么:20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全新增订版)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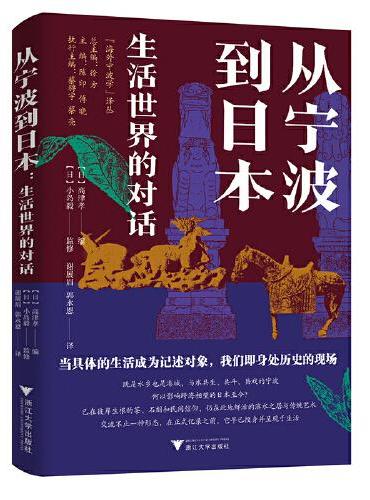
《
从宁波到日本:生活世界的对话
》
售價:HK$
74.8

《
西夏史(历史通识书系)
》
售價:HK$
77.0

《
怪谈:一本详知日本怪谈文学发展脉络史!
》
售價:HK$
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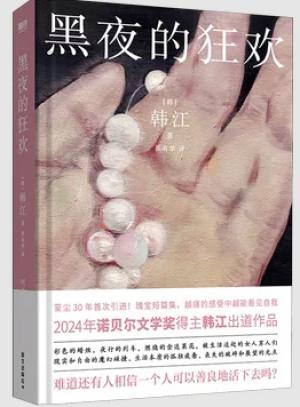
《
韩江黑夜的狂欢: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出道作品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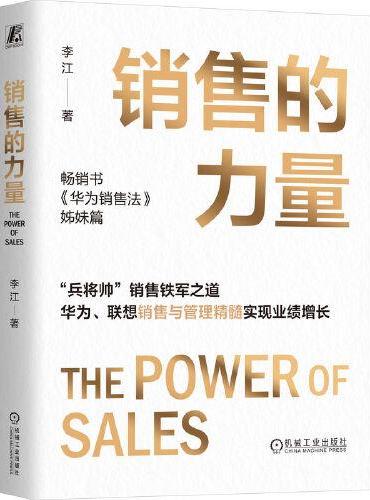
《
销售的力量
》
售價:HK$
97.9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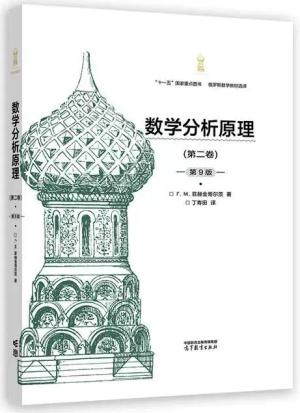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回到乡土,回到记忆,回到痛切的现实。作家阎连科近几年在非虚构写作领域持续发力,醇厚的文字中隐含着精神的苦痛,令读者感同身受,《一个人的三条河》这本关于故乡的存在之书同样如此。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 內容簡介: |
《一个人的三条河》是一部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沉重之书,字里行间浸透着普通中国人的苦辣酸甜。
作者阎连科以自己出生的村落为基点,描写了从家族至亲到儿时伙伴等几十种或悲或喜的人生。这块如同当下中国缩影的小小的中原之地,从不出产成功和胜利,只诉说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存在与消逝,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艰苦劳作、长久病痛、短暂欢愉和生离死别。
《一个人的三条河》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 關於作者: |
|
阎连科,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黄》《日光流年》《受活》《坚硬如水》《为人民眼务》《丁庄梦》《风雅颂》和《四书》等十余部。曾先后获国内外各种小说奖二十余次,作品被译为日、韩、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等二十几种语言,发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在国外最具影响也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
|
| 目錄:
|
想念父亲
父亲的树
过年的母亲
大姐
早逝的两个同学
那个走进洛阳的少年
感谢祈祷
常念那些人
一桩丑行
三个读书人
村头的广告栏
过年几句话
一辆邮电蓝的自行车
我是谁
掏鸟窝
操场边的记忆
葡萄与葫芦
二胡与儿子
镇上的银行
老师!老师!
尘照
病悟
最初的启悟
楼道繁华
条案之痛
我本茶盲
平凹说佛
一个人的三条河
|
| 內容試閱:
|
一个人的三条河
生命与时间是人生最为纠结的事情,一如藤和树的缠绕,总是让人难以分出主干和蔓叶的混淆。当然,到了秋天到来之后,树叶飘零,干枯与死亡相继报到,我们便可轻易认出树之枝干、藤之缠绕的遮掩。我就到了这个午过秋黄的年龄,不假思索,便可看到生命从曾经旺茂的枝叶中裸露出的败谢与枯干。甚至以为,悦然让我写点有关作家与死亡、与时间的文字,对我都是一种生命的冷凉。但之所以要写,是因为我对她与写作的敬重。还有一个原因,是朋友田原从日本回来,告诉我一个平缓而令人震颤的信息,他说谷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谈到生命与年岁时说到:“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富有朝气、卓有才华的诗人兼翻译家田原,年年回来总是给我带些礼物。我以为他这次传递的信息,是他所有礼物中最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在日本的亚洲文学,或说世界文学,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树,约是最为醒目的链环。他们三个人中,诗人谷川俊太郎年龄最长,能说出上边的话,一是因为他的年岁,二是因为他的作品,三是他对自己作品生命的自省和自信。由此我就想到,于一个作家而言,关于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生命,可从三个方面去说: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时间,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时间,三是他作品中虚设的生命时间。
自然的生命时间,人人都有,无非长短而已。正因为长短不等,有人百岁还可街头漫步,有人早早夭折,如流星闪逝。这就让活在中间的绝大多数,看到了上苍对人的生命之无奈的不公,滋生的人类生命本能最大的败腐,莫过于对活着的贪求与渴念,因此膨胀、产生出活着的无边欲望和对死亡莫名的恐慌。我就属于这绝大多数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在北京,最怕去八宝山那个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和病人。十几年前,我的同学因为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在京的同学,都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唯独我不敢去那儿和他最后见上一面。可是结果,大家去了,在伤感之后,依然照旧地工作和生活,而我却每天感到隐隐的头痛头胀,严重起来如撕如裂,于是怀疑自己也有脑瘤,整整有半年时间,不写作,不上班,专门地托亲求友,去医院,找专家,看脑神经、脑血管和大脑相关的各个部位。单各种CT
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医院和专家,也都不惜你的银两,看见小草就说可能会是一株毒树,不断地引领你从感冒的日常遥望癌症的未来,直到最后在北京医院求见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脑瘤专家,他在比对中看完各种片子,淡淡问我:“你看病自费还是报销?”我说:“全是自费。”他才朝我一笑,说你的头痛头胀,还是颈椎增生所致,回家按颈椎病按摩去吧。
实话说,我常常为死亡所困,不愿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现实中以什么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义。躲避这个问题,如史铁生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弄明的执著一样。比如写作,起时是为了通过写作进城,能够逃离土地,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样。后来,通过写作进城之后,又想成名成家,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周围的人有所差别。可到了中年之后,又发现这些欲望追求,与死亡比较,都是那么不值一提,如同我们要用一滴水的晶莹与大海的枯干去较真而论。诚实坦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里就有种灰暗的疼痛,会有种大脑供血不足的心慌。
就是二三年前,北京作协的老作家林斤澜先生因病谢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回来后还连续三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现在,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继续写作,我就对人说:“写作是为了证明我还健康地活着。”我不知道这句话里有多少幽默,多少准确,只是觉得很愿意这样去说。因为我不能说:“我写作是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样会觉得太过正经,未免多有秀演。可我把死亡和写作,把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我实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到更为贴切,更为准确,又可信实的某种说辞。我常常在某种矛盾和悖论中写作。因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写作,而又在写作中反复地、重复地去书写死亡。
《日光流年》我说是为对抗死亡而作,其实也可以说是因恐惧死亡而悠长地叹息。《我与文辈》中有大段对死亡浅白简单的议论,其实也是自己对死亡恐惧而装腔作势的呐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间、在什么年岁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谷川俊太郎先生,在年近八十岁时说了“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那样的话,让我感到温暖的震撼。这句对自然生命与未来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会像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在今后的日子里,照亮我之生命与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让我敢于正视死亡,如正视我家窗前一棵树木的岁月枯荣。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视为一条某一天开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于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等等相类似的职人而言,从这条河流会派生出另外的一条河流来。那就是你活着时创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时间。曹雪芹活了大约四十几岁,而《红楼梦》写就约近250年,似乎今天则刚入生命盛期。没有人能让曹雪芹重新活来,腐骨重生,可也没有人有能力让《红楼梦》消失死去,成为废纸灰烬。卡夫卡41岁时生命消失,而《城堡》《变形记》却生命蔓延不衰,岁月久长久长。他们在活着时并不知自己的作品会生命久远,宛若托尔斯泰活着时,对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充满信心一样。而一个画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长命百岁,并不等于他不理想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
一个作家之所以要继续写作,源源不断,除了生存的需求,从根本去说,他还是相信,或者侥幸自己可以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来。如果不怕招人谩骂,我就坦然我总是存有这样侥幸的莽撞野愿。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倍力无功,如一个一生长跑的运动员,到死你的脚步都在众人之后。你的冲刺只是证明你的双脚还有力量的存在,证明你在长跑中知道掉队但没有选择放弃和退出。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鲁迅所歌颂的“最后一个跑者”罢了。
在中国作家中,我不是写作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挤在跑道上没有停脚者中的一个。跑到最前的,他在年老之后,可以坦然地站在高处,面对夕阳,平静而缓慢地自语:“时间于我,剩下的就是微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因为他们在时间中证实并可以看到自己作品蔓延旺茂的生命,而我于这些证实和看到的,确是不可能的一个未来。何况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何况已经有人断言宣布:“小说已经死亡!”在我来说,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长的生命力,只希望上一部能给下一部带来写作的力量,让我活着时,感到写作对自然生命可以生增存在的意义。
今天,不是文学与读书的时代,更不是诗歌的时代,可谷川俊太郎的诗在日本却可以每部都印一至三万余册,一部诗选集印刷50余版,80多万册,且从他20岁到79岁,60年来,岁岁畅卖常卖。这样我们对诗人已经不可多说什么,就是聂鲁达和艾青都还活着,对今天日本人痴情于某位诗人的阅读,也只能是默默敬仰。这位诗人太可以以“笑着等待死亡”的姿态面向未来。
而我们一生对写作的付出,可能只能换回当年烂俗的保尔·
柯察金的那句名言:“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不为虚度年华而后悔。”如此虚肿的豪言,也是写作的一种无奈。作品的存世,只能说明我们活着时活着的方式。希望自己写出传世之作,实在是一种虚胖的努力,如希望用空气的砖瓦,去砌盖未来的楼厦。但尽管明白如此,我还是要让自己像堂吉诃德一样战斗下去,写作下去,以此证明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某种方式。“决然不求写出传世之作。一切的努力,只希望给下一部的写作不带来气馁的伤害。”这是我今天对写作、对自己作品生命的唯一条约。
努力做一个没有退场的跑者,这是我在没有战胜死亡恐惧之前的一个卑微的写作希望。
有一次,博尔赫斯在美国讲学,学生向他提问说:“我觉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实的,不可思议的。”博尔赫斯对那学生道:“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实。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了,哈姆雷特一定还活着。”这件事情说的是人物的真实和生命,也说的是作品的永久性。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探讨的是作品和作品中的内部时间。作家从他的自然生命之河中派生出作品的生命河流。而从作品的生命河流中,又派生出作品内部的时间的生命。作品无法逃离时间而存在。故事其实就是时间更为繁复的结构。换言之,时间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命脉。故事无法脱离时间而在文字中存在。时间在文字中以故事的方式呈现是小说的特权之一。
20世纪后,批评家为了自己的立论和言说,把时间在小说中变得干枯、具体,如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具又一具的木乃伊。似乎时间的存在,是为了写作的技术而诞生;似乎一部伟大的作品,在写作之初,首先要考虑的是时间存在的形式,它是单线还是多线,是曲线还是直线,是被剪断后的重新连接,还是自然藤状的表现。总是,时间被搁置在了技术的晒台上,与故事、人物、事件和细节可以剥离开来,独立地摆放或挂展。时间愈要清晰而变得更加模糊,让读者无法在阅读中体会和把握。而我愿意努力的,是与之相反的愿望和尝试,就是让时间恢复到写作与生命的本源,在作品中时间成为小说的躯体,有血有肉,和小说的故事无法分割。我相信理顺了小说中的时间,能让小说变得更为清晰。在理顺之后,又把时间重新切断整合,会让批评家兴趣盎然。可我还是希望小说中的时间是模糊的,能够呼吸的,富于生命的,能够感受而无法单单地抽出评说晾晒的。我把时间看做是小说的结构。之所以某种写作的结构、形式千变万化,是因为时间支配了结构,而结构丰富和莫定了故事,从而让时间从小说内部获得了一种生命,如《哈姆雷特》那样。
人的命运,其实是时间的跌宕和扭曲,并不是偶然和突发事件的变异。
我们不能在小说中的人生和命运里忽视时间的意义。时间在根本上左右着小说,只有那些胆大粗疏的写作者,才不顾及时间在小说中的存在。理顺时间在小说中的呈现,其实就是要在乱麻中抽出头绪来。有了头绪,乱麻会成为有意义的生命之物。没有头绪,乱麻只能是乱麻和垃圾堆边的一团。我的写作,并不是如大家想的那样,要从内容开始,“写什么”是起笔之源。而恰恰相反,“怎么写”是我最大的困扰,是我的起笔之始。而在“怎么写”中,结构是难中之难。在这难中之难里,时间的重新梳理,可谓是结构的开端。所以,我说“时间就是结构,是小说的生命。”我用小说中的时间去支撑我的作品,用作品的生命去丰富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样式和意义。反转过来,在自然生命中写作,在写作中赋予作品存世呼吸的可能,而在这些作品内部虚设的时间中,让时间成为故事的生命。这就是一个作家关于时间与死亡的三条河流。生命的自然时间派生出作品的存世时间。作品中的虚设时间获得生命后反作用于作品的生命;而作品的生命,最后才可能让一个作家在年迈之后,面对夕阳,站立高处,可以喃喃自语道:
“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P190-1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