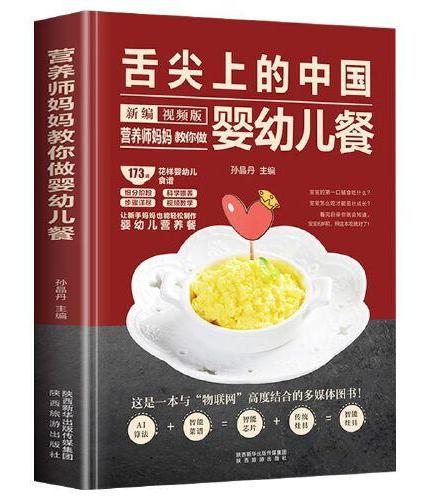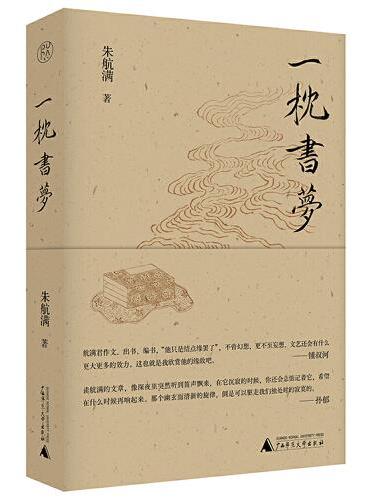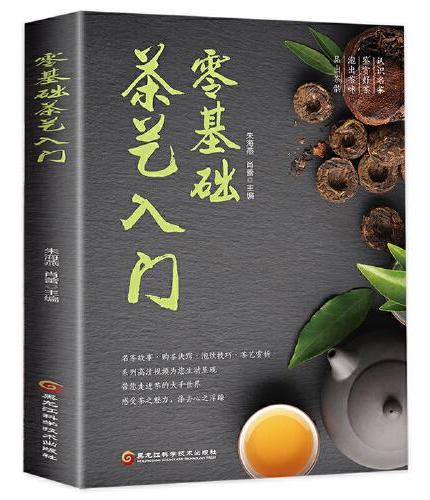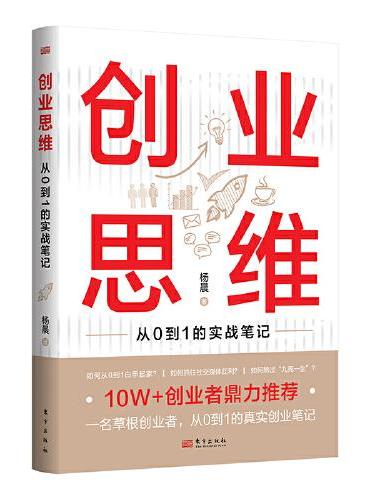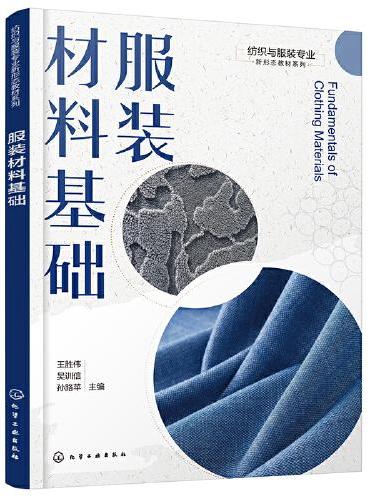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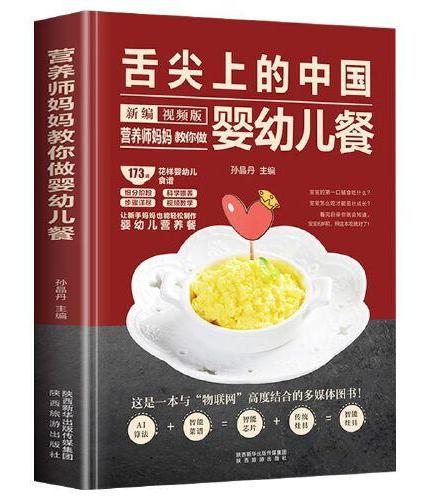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HK$
63.8

《
Scratch创意编程进阶:多学科融合编程100例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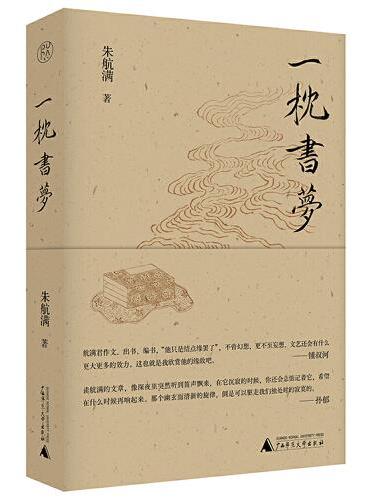
《
纯粹·一枕书梦
》
售價:HK$
7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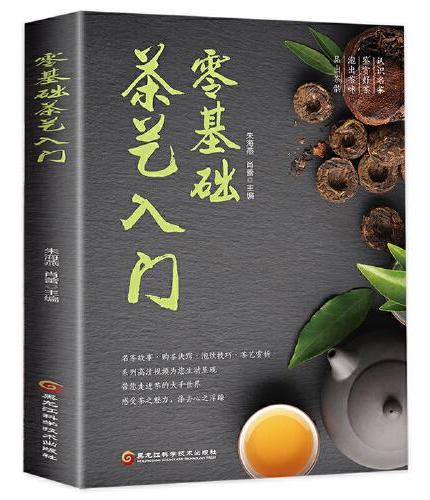
《
新版-零基础茶艺入门
》
售價:HK$
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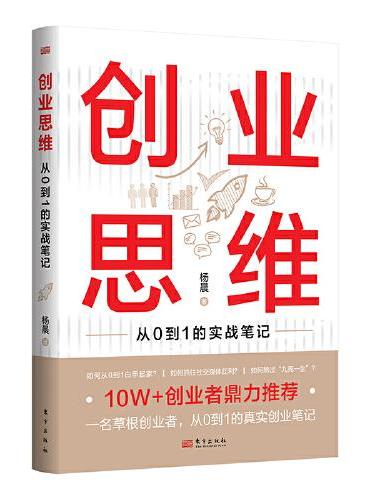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HK$
76.8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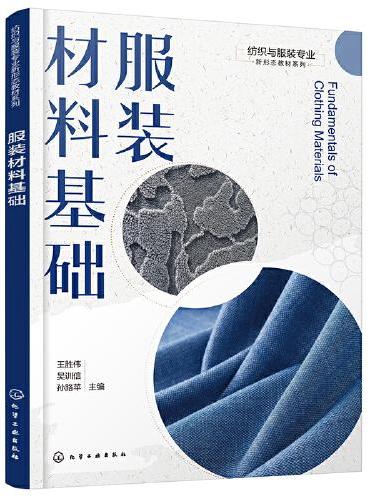
《
服装材料基础
》
售價:HK$
63.8

《
国家名片C919(跟踪十余年,采访百余人,全景式呈现中国大飞机C919,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就)
》
售價:HK$
140.8
|
| 編輯推薦: |
《安拉,别为我哭泣》是战争下的阿富汗妇女苦难生活与坚强求生的真实写照。女主人公锡林-戈尔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开始躲避战乱,可是当她从一个懵懂的少女成长为白发染鬓的老妇,战争也不曾结束。面对无休止的战争、随处可见的死亡、接二连三的屈辱、亲人的离散、被强暴而生下的小孩、不堪重负逃离的丈夫……她用纤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真正的恐惧不是死亡,更非苟活,而是活着的艰辛与肩头的重量。
就算全世界都坍塌了,也不能放弃活下去的希望。
|
| 內容簡介: |
这是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故事,这是无数阿富汗女人的故事,这是关于生命、信仰、权利、反抗、责任与希望的故事……
打从锡林-戈尔记事起,她的国家便遭受着战争的侵袭。她和家人就总是在逃亡的路上,从一个地方逃往另一个地方,从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去哪里呢?又有什么区别?是啊,哪里都一样。这一切,她无从选择。
她用赤裸的双脚行走在阿富汗的山峰、峡谷、沙漠之间,也曾踏上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土地。在几十年的逃亡中,死亡、饥饿、屈辱……如影随形,当遭受非人的蹂躏与折磨,她也曾绝望,也曾轻生,也曾放肆地发疯,却终究没有倒下。她迅速成长并觉醒,面对无尽的苦难与贫穷,面对胆小、懦弱、没有责任心的丈夫,她毅然支撑起了整个家庭。岁月能够无情地雕刻眼角冷酷地涂抹华发,却动摇不了那个坚毅的灵魂。
|
| 關於作者: |
丝芭?沙克布(Siba
Shakib)出生于伊朗的德黑兰。她信仰波斯教,熟悉阿富汗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作为作家和纪录片制作人的她曾在阿富汗工作了六年之久。她为德国电视台(ARD)制作的纪录片非常成功,被视为阿富汗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见证。现生活在德国、美国和意大利。
|
| 目錄:
|
故事缘由 /001
芬芳的花儿和长有胎痣的姐姐 /007
一个穿着暴露的妇女、一个字母和一点自由 /017 摩纳德和阳光 /031
投降和俄国人的撤退 /043
穆斯林游击队、内战和再次逃亡 /045
一次意外和慷慨大方的走私头目 /071
又一个孩子,又一次逃亡 /083
山、石、女人 /093
阿扎丁娜和一次小小的反抗 /117
一个牺牲者和一场婚礼 /139
一个崭新的国度和一颗纸做的心 /167
让孩子们正正经经吃饭和监狱的故事 /189
血红色的花和王后 /199
老屋、坟墓和疯嫂子 /215
有故事的王后 /225
丝摩芙和残存的首都 /233
抽鸦片的摩纳德和孤儿院 /249
破衣烂衫的女人和一点点山羊奶 /261
两个兄弟、北方和慈祥的外祖母 /263
致谢 /267
|
| 內容試閱:
|
故事缘由
姓名?
锡林-戈尔。
这是你的孩子吗?
是的,Bale。
这个也是吗?
是的,Bale。
那这个也……
是的,Bale。
那边那两个男孩都是?他们也是……兄弟俩?
是的,都是。纳维德和纳比,都是我亲生的儿子。
边防官员马赖克虽然满脸狐疑,但还是在那张薄薄的纸上盖了章。那张纸已经被锡林-戈尔攥了几个小时,完全被汗水浸湿了,皱巴巴的。
到后面去!马赖克一本正经地命令道。把这张纸拿给我同事看,就说是马赖克先生给你的,这样就行啦。去拿你的口粮吧,一袋给你男人,一袋是你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人一袋。明白了吗?一人一袋。
女人的脸完全被遮住了,眼前的面纱过于细密,令我无法看清她朦胧的眼神。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她的愤怒、羞愧和屈辱。虽然不知道她是否在看着我,我始终微笑着,试图表达一种友善和理解。她应该能知道吧,我和马赖克不是一伙的,我是站在她这边的。
你都看到了吧?马赖克问我,就好像我是他的老朋友、亲戚,甚至家里人一样。他这么做,似乎在暗示我们是相互信任的伙伴。他和我是一头的,而我们周围的人们是另一头的。我向后退了一步,不再看他。
马赖克很清楚自己的好运,他没有被推到命运的另一端。他不用担心口粮,不需要盖章、批准和同胞的仁慈之心。这一次,这一次的他是幸运的。这一次他得到了工作,成了掌握特权的人。
自从联合国在这里为从伊朗返回的阿富汗人建造了营地,马赖克每月可以赚到差不多六十美元,这些钱足以养活他自己一家和他兄弟那一大家子人。还有些返乡的人为了减轻负担,会沿途扔掉一些口粮,如果他碰巧捡到了这些无主的麦子,就能又赚一大笔钱了。
你都看见了吧?他又煞有介事地重复着。
嗯,我干巴巴地应着,就好像我对那个叫锡林-戈尔的女人的命运毫不感兴趣一样,那个手里攥着潮湿的纸条、带着四个好像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的女人。马赖克必定很失望,不过他期待的眼神在我近乎孩子气的固执中消失了。
马赖克想跟我说什么,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而此时,他的同胞们排着长队等着他盖章,太阳直射着他们脚下的沙地。
他可能想告诉我,这几个孩子都是锡林-戈尔借来的,为了多分一些口粮。待会儿她就会把这些小可怜儿赶走,而他,马赖克,到时候会救回这些孩子,还会考虑把他们安置在哪里。他也可能会说,锡林-戈尔和其他很多阿富汗女人一样,出卖过自己的身体,和不同的男人生了这些孩子。
马赖克先生,我抢在他前面说,很抱歉。这儿太热了,风又大,我想找个阴凉的地方去待一会儿。非常感谢您允许我参观您工作的地方。
可是您还什么都没有看到啊,马赖克立刻抗议了。
我过会儿再来,我撒了一个小谎,随即便消失在那些蓝色塑料帐篷中间。我不希望马赖克知道我去了哪儿,去和谁交谈。
我担心的没错,那四个似乎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已经走远了,我后悔没有仔细看看锡林-戈尔的鞋。鞋子是辨别这些女人的唯一标志。一块打着褶子的蓝布把女人的身体兜头包住,裹得严严实实,掩盖了所有女人的不同,也夺去了她们的尊严。我怎样才能找到锡林-戈尔呢?这里到处都是蓝色的大袍子,时而被风吹得紧贴在女人瘦弱的身体上,时而膨胀起来像个气球,要把这些女人带到天上去。我寻寻觅觅,渴望能从细纱后面的眼睛里看到这些人活生生的灵魂。
我无助地呆站在那里,身边有无数的袍子来回穿梭。我已经忍无可忍啦。一个半月以来我一直在阿富汗,现在已经筋疲力尽。风无止境地刮着,包裹着灰尘,炙热的太阳烧烤着大地,这一切都让人无法呼吸。现在我成了懦夫,不是吗?我不再想听那些人的故事,他们失去了一切,仅剩下恐惧、饥饿、疼痛、贫苦、疾病,当然还剩下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希望一切还能变好。
也许我只是应该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去。也许我应该找一个空帐篷躺进去睡上一觉。我还可以搭上一辆开回边境运输新难民的车子,那么今晚我就能回到生我养我的伊朗,回到那个舒适的花天酒地的西方世界了。
但我整个人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丝毫挪不动步子,只能站在焦灼的太阳下面无所适从。疲惫就像是一件蓝色的纱袍,将我缠住了。
La—elah—ha—el—allah(真主保佑)。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这是我的孩子。看在真主的分上,放过我吧。
我的知觉在瞬间凝固,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请您原谅。我口干舌燥,才说了一句就再也发不出声音来。我死死地盯着对面的纱袍,直到终于可以继续讲话。我只是在这里转转。我不为联合国工作,也不是其他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我在这里,只是因为……
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我想观察、拍摄并描写你们的困苦?只因为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只有看到在世界上遥远的不幸后才能感知自己的心跳?只因为我以为,如果有人能讲述这悲惨的一切,就会有人来帮助你们?特别是当真主把你们当做女孩子送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因为我……
你还好吧?一个穿着袍子的人问道。一只手从袍子下面伸出来,撩起我的袖子,并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
这不是真的,我想。我站在沙漠中间,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像牲口一样被赶上大卡车,而这个女人却问我好不好。
我注视着这些人,他们逃出来的时候,故乡已不完整,而他们将要回去的故乡也不会是完整的。这些素不相识的女人、孩子、男人一直都在逃亡。他们埋葬了女儿和儿子后又要埋葬自己的父母、爱人或兄弟姐妹。他们没有房子,没有吃穿,甚至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有些女孩和男孩只剩下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甚至没有胳膊和腿。人们体弱多病,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那些男人杀掉了其他男人,而自己也看到了死亡。那些宁愿自己去死的女人,却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
我已经猜到了,锡林-戈尔平静地说。她的声音温柔地划过我的心际。
什么?我依然神志不清。你猜到了什么?
你不属于任何援助机构。你讲我们的语言。你是谁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锡林-戈尔的手很有力,仍然放在我的手臂上。她蹲下身来,拉着我一起坐在沙地上。
我在写一本书,我说,试图透过面纱上细密的网眼找寻到她的眼睛。我已经想好了接下来说什么。
一本关于阿富汗的书。关于我们?人们嘲笑我,嘲笑我要写这个一无所有,只剩下饥饿、贫苦、战争和死亡的国家。这儿有什么可写的?有谁愿意读这样一本书啊?
我会读的,锡林-戈尔说。从前俄国人在的时候,我上过学,也识字。除了教科书以外,我一共读过三本半书。第一本是我自己买的,第二本是我的女老师送我的,而第三本只有一半。那是首都被炸后我在废墟里找到的。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另外半本。我多想读完整个故事啊,那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有关一个小女孩,她……唉,更多的我也不知道了。后来我唯一的、真正的女朋友送了我一本书,她是一名医生,我在逃亡中的一个村庄里认识了她,我还为她工作过。
戴着面纱的锡林-戈尔注视着我,我感觉她正在解读我,就像在读一本书。我不用说话,不用解释,她可以读懂我。
最后她把手从我的臂上拿掉,在我的皮肤上留下了一个潮湿的印记。我不想擦干它,就让太阳把它晒干好了。
一本书,锡林-戈尔说。她的头巾丝毫未动。
我微笑着望着那蓝色的头巾。
我该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吗,让你把它写进你的书里?戴着头巾的锡林-戈尔问我,你要听吗?
她的问题像是警告,又像是一种威胁。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回答“是”,为什么我的目光转向了那些将风尘仆仆的阿富汗人从伊朗带回来,随即又丢弃在蓝色的塑料帐篷中的大卡车呢?我毫无头绪。锡林-戈尔用手托住我的下巴,把我的头转向她,强迫我注视她头巾下的双眼,再一次问我,你想听吗?
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锡林-戈尔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如果我回答“是”,那么我从这个早晨开始,就进入了她的故事和生活,然后我们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很多年,也许是永远。
是,我想是的,我含笑对她说,然后握住她依然托着我脸庞的手。
我很高兴,我回答了“是”。
锡林-戈尔和我遇到的其他阿富汗女人不同。锡林-戈尔像是一棵大树,一棵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挺拔有力的白杨。她看透一切,理解一切,明白一切,也讲述一切。
我所认识的阿富汗女人从不会这么开放,她们不愿提及自己的生活,更不会讲自己和丈夫的关系。锡林-戈尔告诉我一切她能回忆起来的故事,精确而详细,好像她希望等自己离开人世以后,她的故事还能留下来。对她而言,我是否提问并不重要,她用自己的节奏和速度讲述着生命里的故事。锡林-戈尔的声音时而像呼啸而过的狂风卷走一切,时而像清新温柔的微风拂过面庞;时而像春天里温暖和煦的太阳温暖心房,时而像沙漠里冷酷无情的太阳熊熊燃烧;时而像绵绵细雨唤醒了我的思想,时而像一场暴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地上,然后变成激流荡除一切障碍。
锡林-戈尔的故事并不特殊,听上去似乎荒谬之极,但实际上却是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妇女已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故事。
在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个难民营,还有那些城市和乡村,整个国家,到处充斥着和锡林-戈尔一样的女人、孩子和男人。他们一再创造希望,一再重新起程,又一再相信一切都会变好。人们从开始就相信一切会变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