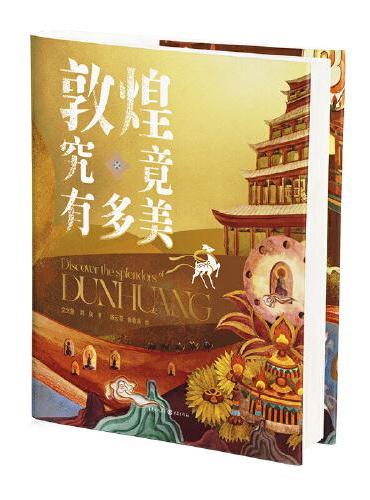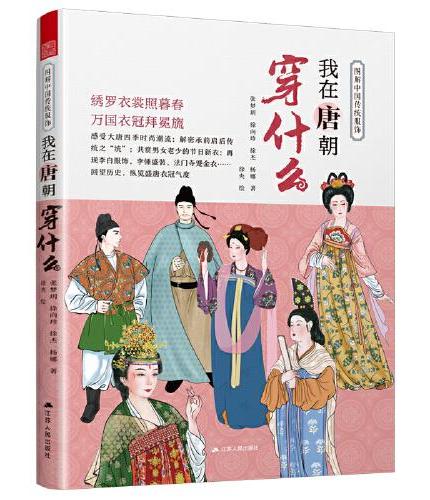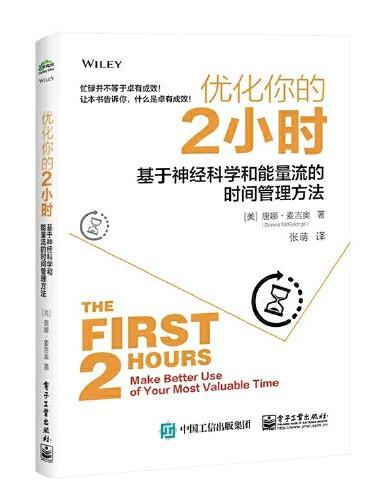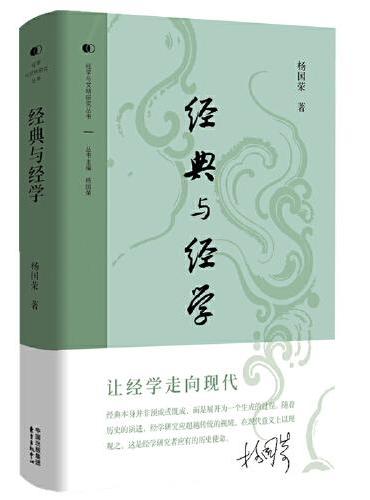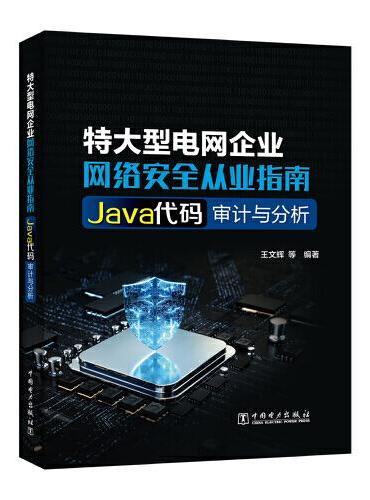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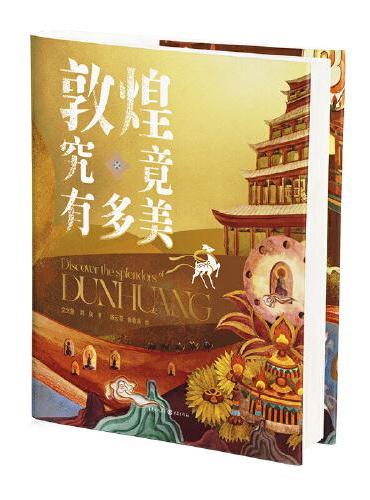
《
敦煌究竟有多美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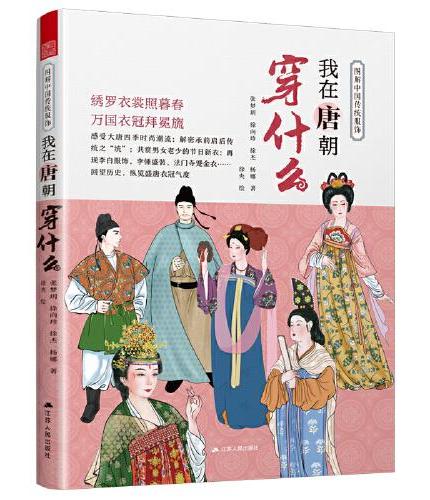
《
我在唐朝穿什么(图解中国传统服饰 服饰搭配 汉服研究 古代服饰)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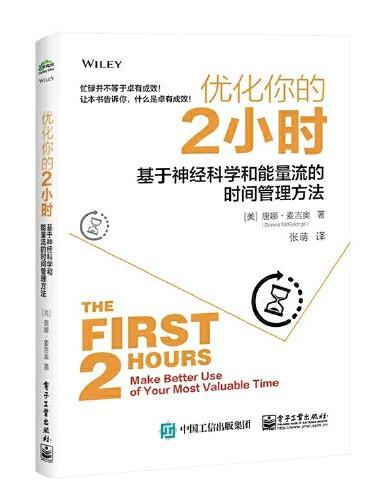
《
优化你的2小时 : 基于神经科学和能量流的时间管理方法
》
售價:HK$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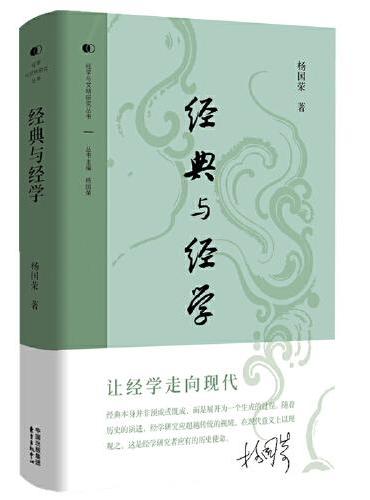
《
经典与经学
》
售價:HK$
85.8

《
颧种植理论与临床
》
售價:HK$
437.8

《
《胡适留学日记》汇校本(全四册)
》
售價:HK$
7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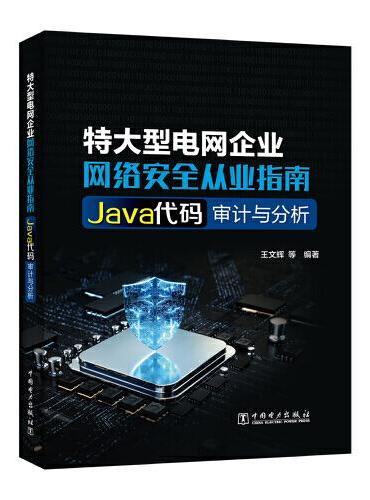
《
特大型电网企业网络安全从业指南 Java代码审计与分析
》
售價:HK$
173.8

《
心灵哲学
》
售價:HK$
140.8
|
| 編輯推薦: |
原本贾平凹?长篇小说系列,部分手稿版与成书的相应映衬,韵味浓厚
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谜一样的村庄,一群卑微的人和一些琐碎的事
乡土小说的传世经典
纯文学、乡土写作“最后的大师”
|
| 內容簡介: |
|
本书讲述了靠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农村青年高子路携妻回到故乡,与往昔故人之间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体现了封闭守旧的环境所导致的人的退化和改革开放对人的改良。高老庄是高子路的故乡,为了给父亲做三周年的祭奠,高子路同再婚妻子西夏从省城回到了故乡。原本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大学教授的高子路回到村子后,再次接触到旧的文化、旧的环境和旧的人群立刻使他回到了从前,开始变得保守、自私。此时的高老庄俨然成了一面魔镜,照出了高子路骨子里的固有的习惯,各种冲突和矛盾接踵而至。这部小说展现了大生命、大社会、大文化三个空间,却落笔于最底层、最日常、最琐碎的生活细节,是贾平凹小说创作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
| 關於作者: |
贾平凹,陕西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
奇才,当代中国富有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世界级作家。被誉为文学“鬼才”。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废都》《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高兴》《古炉》等。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曾多次获全国文学奖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等国际大奖。
|
| 內容試閱:
|
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地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稷甲岭常常崖崩,但这一次情形十分严重,黄昏的时候有人看见了一个椭圆形的东西在葡萄园的上空旋转,接着一声巨响,像地震一般,骥林娘放在檐笸上晾米的瓦盆当即就跌碎。双鱼家的山墙头掉下一块砖,砸着卧在墙下酣睡的母猪,母猪就流产了。而镇上所有人家的门环,在那一瞬间都哐啷哐啷地一齐摇动。迷胡叔也是看到了那个椭圆形的飞行物,坚持认为那是一顶草帽,崖崩一定与草帽有关,因为当年他之所以在白云湫杀人,就是也看见过这样的草帽。高老庄镇的镇长,他是有文化的,当然要批评迷胡叔,一面解释这可能是飞碟,近年里在商州地面上已经有过多次发现飞碟的报道,不足为怪;一面察看了崖崩现场,将崖石埋没的三十亩水田写成了五十亩水田和一条灌溉渠的重大灾情报告,紧急申请着县政府的救济。
这天夜里,菊娃抱着双腿残疾的儿子和婆婆在院里看天象,还说着白日的崖崩。就在米碗里插着了三根高香,感念起崖崩埋没了那么多的水田,眼看着就埋没到了祖坟,却没有埋没,这都是神灵的保佑,要不,孩子的爷爷快要过三周年忌日了,那可怎么得了?顺善路过院门口,鼻子凑凑,闻见了高香的荃味,也笑眯眯踅脚进来,听她们提说三周年忌日的事,就问道:“这三周年的祭祀是大过呀还是小过,子路难道还不肯回来吗?”菊娃和婆婆一时都脸上僵住,没了言语。顺善却发起感慨:“上一辈人,或上上一辈人,即使在外干多大的事业,于老家还是要筑一院房子,修一条巷道,造桥建祠,盖戏楼子——风流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七星沟的苏家寨子,木王岭的高阳堡,还有咱高老庄,都是这么形成的镇落。可这些年里苏家寨子又出了个医生,出了一名诗人,北京城里的总书记巡视到那里,县上领导赠送总书记的就是一套医生研制的护阙真元袋,再就是诗人当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十八首颂辞。高阳堡也出了一个县财政局长,一个县办公室主任,两家的房子都盖得前有庭后有院的,镇中建了大市场,方圆十多里的人要去赶集,租赁摊位,在市场的招待楼上可以泡茶和泡烧茶的妞儿。子路已经是省城大学的教授了,大家满以为他要在高老庄大兴土木呀,可他数年竟不回来,这井也不淘,门楼不修,院墙头塌了一豁,好像是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菊娃忙说:“顺善哥你扯到哪儿去了?睡吧睡吧,夜也深了,明日我还替娘去茶坊镇买几斤棉花哩!”顺善嗯了嗯,停止话头,摸摸孩子的脸,说:“伯来了也不问候?叫伯!”孩子瞪着眼,偏是不叫,顺善就又问茶坊镇的棉花是什么价,镇街东头的货栈里新进了一批棉花,成色好,肯定还比茶坊镇的便宜,就走了。顺善一走,菊娃和婆婆还是仰头看着满空繁星,各自默数了一遍,又默数了一遍,一遍与一遍数目不同。坐坐无聊,各自进屋睡去。
菊娃挪坐在了厦房的炕上了,两只鞋子一脱丢下地,不偏不倚,整整齐齐排在一起,但全都底儿朝上。儿子趴在炕沿看着,突然说:“娘,我爹他们要回来了。”菊娃愣住了,拿眼睛直勾勾看起儿子。她希望着儿子再说一句,儿子却钻进被窝睡下了。门外头起了风,风从门道里进来吹动了吊在半空的灯泡,使菊娃的影子在墙上忽大忽小,菊娃一时似乎思量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思量,久久地坐在那里,听野狗在村口土场上叫。天明起来,对婆婆说:“娘,我今日就到店里去住。”娘说:“不是说好去茶坊镇买棉花吗?”菊娃说:“改日去吧。……石头我也得送到他舅家去。”娘说:“改日就改日吧。店里就那一张小床,雇来的彩彩在那儿,两人怎得睡下?你说啥的,石头去你哥那儿?!”菊娃说:“我哥那儿离老黑家近,石头跟老黑爹学针灸,总不能有一阵没一阵的。”娘说:“……这怎么都要走呀?”菊娃说:“石头他爹要回来了。”老太太也愣了,嘴张张,倒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头就低下去,一边用抹布擦柜盖上的米盆面罐儿,擦出油光来,一边说:“子路要回来?谁说子路要回来?子路……”
吃罢早饭,菊娃果真背了石头去了娘家。子路娘在院子里立了一会儿,捉住鸡拿指头塞进鸡屁眼里试有没有颗蛋下,但立即把鸡丢开,进屋翻箱倒柜,寻着了子路早年的一双旧鞋,用绳子系了,吊到红薯地窖里,自言自语道:要回来,就把西夏也给我领回来,让你爹也瞧瞧我儿的日子又回全了!
娘在家里唠叨着,心灵感应,坐在车站台阶上的子路就打了个喷嚏。这个喷嚏打得惊天动地,连站在广场上的那个警察也回头往这边望望,子路有些不好意思,但立即矜持起来,面上平静如水,然后目光放远,瞧起西夏挤进了售票房前的一堆人群里。原本该西夏在这里守护行李子路去买票的,但子路的个子小,挤不到售票窗下,又不想从那些人的胳膊下钻来钻去,西夏就长胳膊长腿地去了。
西夏在人窝里挤得满头大汗,鞋踩脏了,发卡也掉了,好不容易买了票退出来喘气,旁边一个女人一直在看她,说:“这么漂亮的人,该有自己的私家车哩!”西夏说:“是吗?那我就得换老公呀!”那女人白皮净肉地笑了,说:“到哪儿旅游?”西夏说:“回婆家。”女人说:“哪儿的?”西夏说:“高老庄!”说罢自己也嗤地笑了,她想到了猪八戒,《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也是高老庄上的人,西天取经的路上,动不动就要回去。那女人并不知道西夏发笑的意思,听说是去高老庄,就过来把西夏的手拉住,说高老庄是个好地方,她是去过的,而且现在还有个亲戚就在高老庄。西夏便觉亲近,问高老庄都有些什么好玩的,那女人说:有山,山深似海哩,这个时候去,柿饼板栗吃不到,杏子却下树了,你若坐车,路边常有人叫喊买呀买呀,你把一张钱丢下去,卖杏人就把杏子往车上撂,你没有接够数,他们会撵着车跑呀跑的,还给你扔!沟畔里到处有古松,苔藓和蕨草就从树根到树梢附着了长,一嘟噜一嘟噜的藤蔓便垂下来,有红嘴白尾的鸟在里边叫。你见过连翘吗?中药铺里有一味药叫连翘,谁能想到连翘竟长那么大的一蓬,花开得是那般黄,佛黄。西夏就兴奋起来,问还有些什么,那女人说有太壶寺,有一猫腰就能打出一桶水的泉窝,桶里会有七条八条小虾蟆,高老庄人不吃虾蟆。还有白云湫。西夏把扑撒到脸前的乱发拢了拢,问白云湫是什么,那女人说,是个湖,是个沟,是一沟的老树林子,人都说那里住着神仙也住着魔鬼,是天下最怪的地方,但我没去过。女人很遗憾,西夏也陪着她遗憾了,又拢拢又扑撒到了脸上的乱发,骂了一句:“这头发真烦!”女人说,要去高老庄,得剪个短发的,到处是梢树林子,雨后进去捡菌子,长头发就不方便,高老庄的狗都是细狗,一生下来主人就把尾巴剁了。说着从自己头上摘下一只发卡给了西夏。西夏不愿无故接受赠品,谢绝不要,但不行,再要付钱时,女人说这能值几个钱呀,动手帮西夏把头发拢整齐,别上了发卡,直叫道漂亮。西夏谢谢着这位陌路相逢的女人,邀请她去见见子路:说不定论起来,她的那位亲戚还是子路的什么亲戚,世界说大,大得很,说小又小得就那么几个人呢!但那女人却不想去见子路,说她是电视台的记者,得立即去很远的地方出差呀,就拜拜,没在人群不见了。
西夏返回车站的台阶上,子路却不在了那里。举目四顾,他双肩挂着两个大提包,腰弓着,越发矮得像个孩子,在一家小店铺门口和人争执哩。西夏就喊:“子路,子路!”子路过来,一脸的恼怒,晃着手里的空水杯,骂那些小店主啬皮,跑了三家都不愿给他倒一杯白开水的。西夏说:“你给人家掏两角钱,谁不会热情卖给你?”子路说:“要是高老庄,水拿井盛哩!”西夏拿了水杯转身要去买,子路说:“不喝了,气都气饱了,票买到手了吗?”西夏说:“买到了,你猜我见到谁了?”子路说:“谁?”西夏说:“白白净净的,鼻梁上有一颗痣,她说她亲戚也在高老庄。送我了一个发卡,别上好看不好看?”子路说:“好看,你别什么都好看。她亲戚也是高老庄的,怎不领来拉拉话?”西夏说:“人家忙着出差呀,是电视台的记者,人家是记者哩!”子路说:“那算啥的,不就是拿个黑驴往领导嘴里塞着的工作嘛!”西夏说:“这都是教授说的话?”两人就扑扑哧哧笑起来。地道口前的栏杆下坐着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孩子在看着子路和西夏笑,子路和西夏也就笑了。子路和西夏已经不笑了,孩子还在笑着。子路就给孩子做鬼脸儿,把两只耳朵往前拉,撅着嘴,像肥猪的样子,孩子并没有反应,反应的却是孩子的母亲,她微笑着向子路招手。这是一个白面长身的女人,子路就走近去,女人对孩子说:“叫叔叔。”孩子说:“叔叔。”女人说:“让你好好吃饭,你不好好吃,再不好好吃你就只长叔叔这么高!”子路脸腾地红起来。但子路毕竟是教授,他说:“你娘说得对,要好好吃饭哩,个头长不高受人歧视的。”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话没说好,忙抱歉她不是那个意思,子路却严肃地走开了。
两人走进车站,西夏问:“和人家说什么了?”子路说:“她问我做什么事?我说是教授。她说做教授好哇,可怜她只是初中毕业……”西夏说:“瞧着人家漂亮了把什么都说?!”子路说:“她漂亮?你一来这里还有漂亮人?!”子路把两个提包都提过来,小跑着跟在西夏的身后,像个驮驴儿。
后 记
贾平凹
今年我将出版我的文集,一共是十四卷,没有包括过去的《废都》和现在完成的《高老庄》。设计封面的曹刚先生在每一卷上以一个字做装饰,他选用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宁四方”。这是刘邦的诗,二十三个字。瞬间的感觉里,我立即知道我的一生是会能写出二十三卷书的。《高老庄》应该为第十六卷,也就是我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
在世纪之末写完《高老庄》,我已经是很中年的人了。人是有本命年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本命年里莫不是恐慌惧怕,同样,天地运动也有它的周期性,过去的世纪之末景象如何,我们不能知道,但近几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频繁的战争,骚乱,饥荒,瘟疫,旱涝,地震,恶性事故和金融危机,使得整个人类都焦躁着。世纪末的情绪笼罩着这个世界,于我正偏偏在中年。中年是人生最身心憔悴的阶段,上要养老,下要哺小,又有单位的工作,又有个人的事业,肩膀上扛的是一大堆人的脑袋,而身体却在极快地衰败。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除过坐牢,我自信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我也开始相信了命运,总觉得我的人生剧本早被谁之手写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时候,有笑声在什么地方轻轻地响起。《道德经》再不被认作是消极的世界观,《易经》也不再是故弄玄虚的东西,世事的变幻一步步看透,静正就附体而生,无所慕羡了,已不再宠辱动心。
一早一晚都在仰头看天,像全在天上,蹲下来看地上熙熙攘攘物事,一切又都在其中。年初的一个黄昏,低云飞渡,我出门要干事去,当一脚要踏下去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一只虫子就在脚下活活地蠕动,但我的脚因惯性已无法控制,踏下去就把它踏死了。我站在那里,悲哀了许久,忏悔着我无意的伤害,却一时想到这只虫子是多么像我们人类呀,这虫子正快乐地或愁苦地生活着,突然被踏死,虫子们一定在惊恐着这是一场什么灾难呢?也就在那个晚上,我坐在书房里,脑子里还想着虫子们的思考,电视中正播放着西藏的山民向神灵祈祷的镜头,蓦地醒悟这个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着神灵和魔鬼的,之所以种种奇离的事件发生,古代的比现代的多,乡村的比城市的多,边地的比内地的多,那都是大自然的力的影响。类似这样的小事,和这样的小事的启示,几乎不断地发生在我的中年,我中年阶段的世界观就逐渐变化。我曾经在一篇短文里写过这样的话:道被确立之后,德将重新定位。于是,对于文学,我也为我的评判标准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惊异了。当我以前阅读《红楼梦》和《楚辞》,阅读《老人与海》和《尤里西斯》,我欣赏的是它们的情调和文笔,是它们的奇思妙想和优美,但我并不能理解他们怎么就写出了这样的作品。而今重新捡起来读,我再也没兴趣在其中摘录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动我的已不在了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说隐于文字之后的作家的灵魂!偶尔的一天我见到了一副对联,其中的下联是:“青天一鹤见精神”,我热泪长流,我终于明白了鹤的精神来自于青天!回过头来,那些曾令我迷醉的一些作品就离我远去了,那些浅薄的东西,虽然被投机者哗众取宠,被芸芸众生的人云亦云地热闹,却为我不再受惑和所骗。对于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追求使我越来越失却了往昔的优美,清新和形式上的华丽。我是陕西的商州人,商州现属西北地,历史上却归之于楚界,我的天资里有粗犷的成分,也有性灵派里的东西,我警惕了顺着性灵派的路子走去而渐巧渐小,我也明白我如何地发展我的粗犷苍茫,粗犷苍茫里的灵动那是必然的。我也自信在我初读《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时,我立即有对应感,我不缺乏他们的写作情致和趣味,但他们的胸中的块垒却是我在世纪之末的中年里才得到理解。我是失却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我对于我写作的重新定位,对于曾经阅读过的名著的重新理解,我觉得是以年龄和经历的丰富做基础的,时代的感触和人生的感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深切休会的,即使体会,站在了第一台阶也只能体会到第二台阶,而不是从第一台阶就体会到了第四第五台阶。世纪末的阴影挥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们在吟唱着他们的青春的愁闷,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愁,满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们唠唠叨叨着所得的工钱和物价的上涨,他们关心的仅是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人。大风刮来,所有的草木都要摇曳,而钟声依然是悠远而舒缓地穿越空间,老僧老矣,他并没有去悬梁自尽,也不激愤汹汹,他说着人人都听得懂的家常话。
《高老庄》落笔之后,许多熟人和生人碰见了我,总在问我又写了什么?我能写什么呢,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和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不会写历史演义的故事,也写不出未来的科学幻想,那样的小说属于别人去写,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但我有致命的弱点,这犹如我生性做不了官虽然我仍有官衔一样,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我却应该算作一位诗人。对于小说的思考,我在许多文章里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后记里也有过长长的一段叙述,遗憾的是数年过去,回应我的人寥寥无几。这令我有些沮丧,但也使我很快归于平静,因为现在的文坛,热点并不在小说的观念上,没有人注意到我,而我自《废都》后已经被烟雾笼罩得无法让别人走近。现在我写《高老庄》,取材仍是来自于商州和西安,但我绝不是写的商州和西安,我从来也没承认过我写的就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对将题材分为农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个行业。我无论写的什么题材,都是我营建我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我终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两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西安官方传统文化孕育了我作为作家的素养,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中淫浸越久,越知传统文化带给我的痛苦,越对其的种种弊害深恶痛绝。我出生于一九五二年,正好是二十世纪的后半叶,经历了一次一次窒息人生命的政治运动和贫穷,直到现在,国家在改革了,又面临了一个速成的年代。我的一个朋友曾对我讲过,他是在改革年代里最易于接受现代化的,他购置了新的住宅,买了各种家用电器,又是电脑,VCD,摩托车,但这些东西都是传统文化里的人制造的第一代第二代产品,三天两头出现质量毛病,使他饱尝了修理之苦。他的苦我何尝没有体会呢,恐怕每一个人都深有感触。文学又怎能不受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呢?我或许不能算时兴的人,我默默地欢呼和祝愿那些先蹈者的举动,但我更易于知道我们的身上正缺乏什么,如何将西方的先进的东西拿过来又如何作用,伟大的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伟人们给了我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在缓慢地,步步为营地推动着我的战车,不管其中有过多少困难,受过多少热讽冷刺甚或误解和打击,我的好处是依然不掉头就走。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却是莲日日生起,盼望着浮出水面开绽出一朵花来。
《高老庄》里依旧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依旧是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我熟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生活,写起来能得于心又能应于手。为什么如此落笔,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昔的秀丽和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这缘于我对小说的观念改变。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什么,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这样的作品是很容易让人误读的,如果只读到实的一面,生活的琐碎描写让人疲倦,觉得没了意思,而又常惹得不崇高的指责,但只读到虚的一面,阅历不够的人却不知所云。我之所以坚持我的写法,我相信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纯形式的文字游戏,我的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人在中年里已挫了争胜好强心,静伏下来踏实地做自己的事,随心所欲地去做,大自在地去做,我毕竟还有七卷书要写。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边城》里说“他或许明日就回来,或许永远也不回来了。”我套用他的话,我寄希望于我的第十七卷书,或者就寄希望于那第二十四卷了。
另,文中的碑文参考和改造了由李启良、李厚之、张会鉴、杨克诸先生搜集整理的《安康碑版钩沉》一书,在此说明并致谢。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日下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