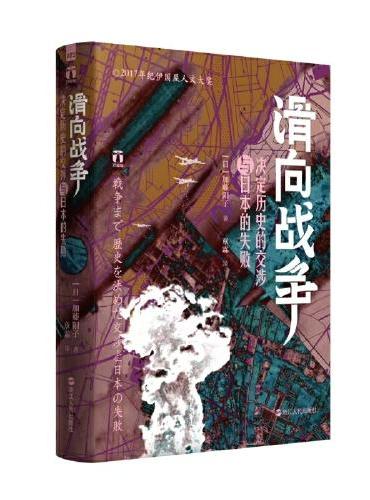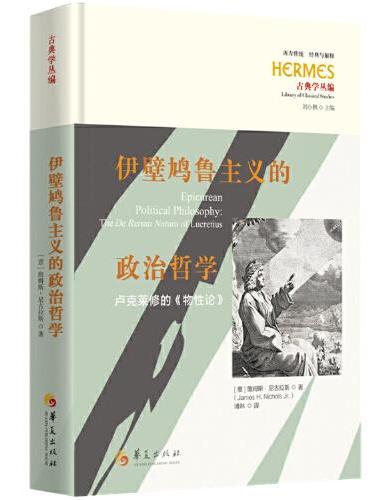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
》
售價:HK$
96.8

《
你可以有情绪,但别往心里去
》
售價:HK$
46.2

《
汴京客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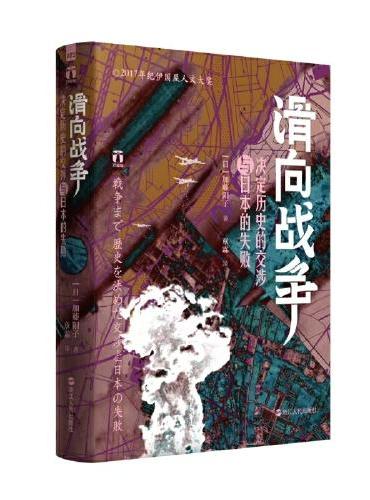
《
好望角·滑向战争:决定历史的交涉与日本的失败
》
售價:HK$
107.8

《
八千里路云和月(白先勇新作!记述我的父亲母亲并及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
售價:HK$
68.2

《
教师助手:巧用AI高效教学(给教师的66个DeepSeek实战技巧,AI助力备课、教学、练习、考试及测评)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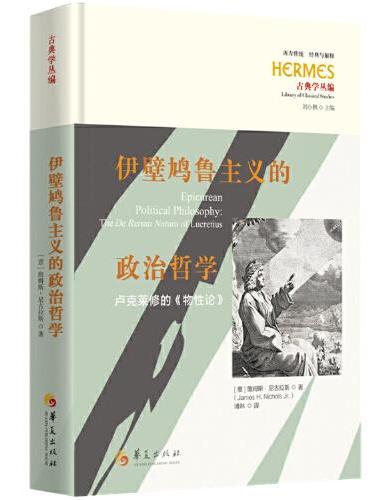
《
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 :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
》
售價:HK$
68.2

《
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新经济结构
》
售價:HK$
152.9
|
| 內容簡介: |
|
透过《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静静的月亮山》,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
| 關於作者: |
|
马知遥,原名马明春,回族,1937年10月生于湖北沔阳县。196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油画专业,师从刘秉江等先生。著名回族作家,油画家。其小说在历次宁夏文学评奖中多有获奖,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
|
| 目錄:
|
古尔邦节
搭伙
四月的河滩
三七
白骟驼
老烈
旅途
黄米干饭
开斋节
静静的月亮山
幺叔
|
| 內容試閱:
|
乌德老汉歪着脖子又朝河边走去,这是第三天了。他扎着头,显得很疲惫,像丢了魂似的。他这架势真像是和谁刚吵完架在发恨在赌气。其实他现在用不着再歪着脖子,他本来就不是歪脖子。庄子里谁都知道他二十年前跟马老师家媳妇舍舍子干过的那桩被别人捉住割掉了左耳朵的事,咋遮掩也遮掩不过去。这事真损,真比他妈坐三年班房更折磨人!
四月,柳树绿了,风中弥漫着阵阵燥热,乌德老汉仍裹着光板子老羊皮袄,手缩在袖筒里,一伙穿牛仔裤、健美裤的尕子、丫头子就觉得很扎眼很滑稽很别扭很不合时宜。他们开心地放肆地取笑:“喂,看,十二点过五分,疯了!”上岁数的人理所当然地会给乌德老汉以同情的眼光,对他们嗤之以鼻:“龟孙们,笑啥?活了狗大个岁数!懂个啥?!”他们理解乌德老汉:他一辈子跟河打交道,好不容易造了条船,又被他外甥子硬给卖了。心里不好受哩,可能要他的老命哩。“婊子养的娃们,还笑哩!”于是,尕子、丫头们不笑了,挤挤眼撇撇嘴走开了。
乌德老汉听见了当做没听见,他犯不着跟娃们计较。他没那份心劲。他只可惜了他那条船,他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憧憬一辈子的梦!
他整个身子整个心都灰灰的乏乏的。
他不管不顾地走自己的路。
偌大的河滩没有路,没有路就到处是路。翻过防洪堤凭你走;各人有各人的走法,各人有各人的习惯;没有自己走法和习惯的外乡人就跟着别人的习惯走;可能是手扶拖拉机、架子车印下的连续不断的带花纹的两行车辙,可能是牲口踩下的时隐时现的蹄坑,可能是鞋底子踏瓷的一条条隐隐约约的灰白的亮光。乌德老汉有一条固定不变的路,这条路与其说是在河滩上倒不如说在他心里。虽然旁人说他那样走太远,他说觉不出来,远不到哪里去。他觉得那样走亲切、踏实,旁的走法他总提心吊胆。
出庄子往下二里地,有一棵很大很大的红柳树,展展地像一座大草垛趴在地皮上,起初他分不清是一棵还是几棵,分不清枝枝干干,像被风随便刮来的,像被土故意掩埋的,孤零零长在河滩上,充满无限的生机。每次下河他都要走到红柳树再向河踅,同时就想起抓养他的大纳自刚:“大是个好人!”那时他六岁。五岁跟爹妈从后套讨饭到石嘴子,冬天爹妈冻死了,他就在石嘴子流浪街头。他觉得回回人心善,常在一家小饭馆乞讨。那天,他见一个五大三粗的大汉,要了一老碗手抓羊肉,就着盐面、醋、蒜,狼吞虎咽地吃,满嘴满手油晃晃的,脸上的筋肉全在动全在忙活。他使劲咽口水,巴望他剩下点皮皮筋筋骨头棒棒。但是他吃得很仔细很在行,连骨头渣渣都不剩。他失望地舔着脏乎乎的嘴唇。那汉子抬起头来发现了他,冲他傻傻地笑了笑就死死地盯上了他。他觉得浑身发毛。汉子走到他面前蹲下,他想躲也躲不脱,一只大手巴掌兜着他的后脑勺,定定地要去捉他鼻子里咬叫着的白狗。“噫,日他妈还舍不得哩!”饭馆子里的人都笑起来,这时他一低头从那人胳膊下溜跑了。他一气跑到河边,他想他准保抓不着他了。他跎蹴在河岸边,望着血红红的黄河水,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船,比房子还大,那上面一定很好耍很舒坦。他想上去试探试探,又怕别人把他当贼扔到河里。他不想去死。他双手抱着腿,下巴搁在膝盖上数着船上大大小小的水缸、瓦罐:一二三四五六……数着数着眼就花了,一个一个圆洞互相乱窜,数不清了。他决心非数清不可:一二三四五六……突然一个人把他抱起来,他的心猛猛一悬,吓出一身冷汗。“好娃,把我寻了个苦,你倒是自己跑来了!”他扭头一看:就那给自己揩鼻子的大汉!
他把他放下,抓住他的两只手,抓得很疼。“尕子,”他望着他的眼睛,“你给我当儿子,咋话?”他不敢看他,只低着头看自己的脚趾头拱泥,像土虫打洞。
“说话呀,成不成?”那人抖他的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