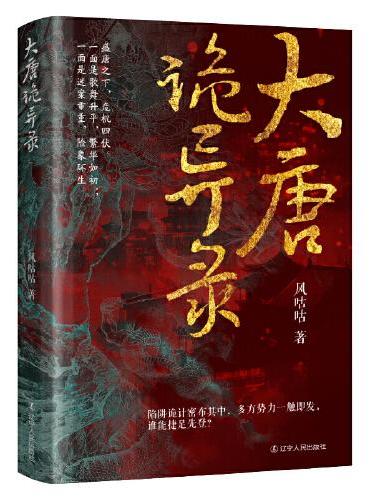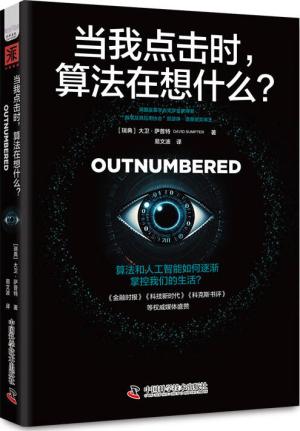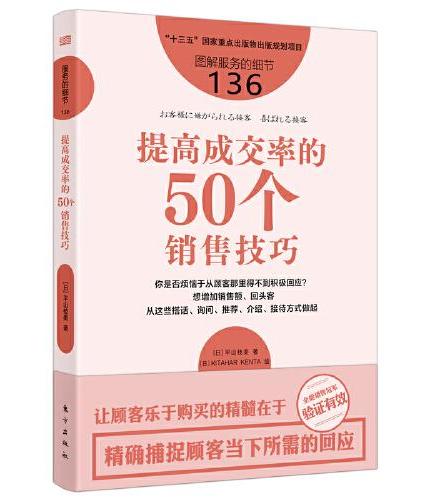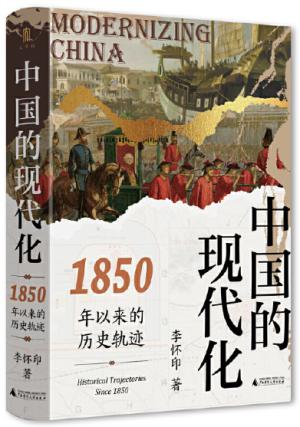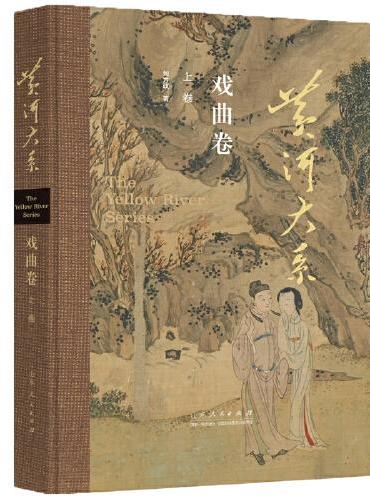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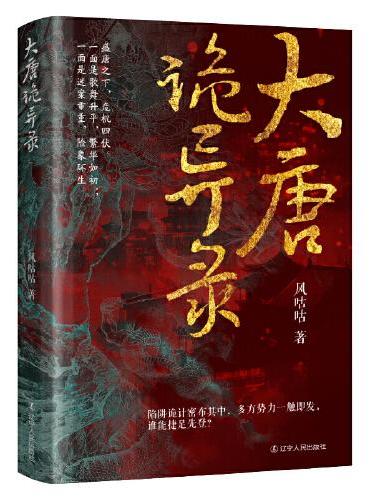
《
大唐诡异录
》
售價:HK$
55.8

《
《证券分析》前传:格雷厄姆投资思想与证券分析方法
》
售價:HK$
1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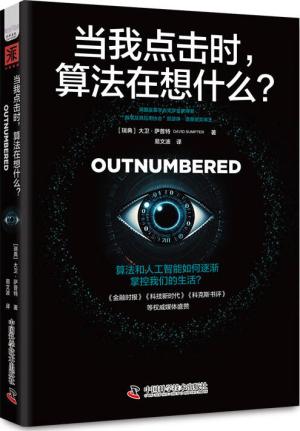
《
当我点击时,算法在想什么?
》
售價:HK$
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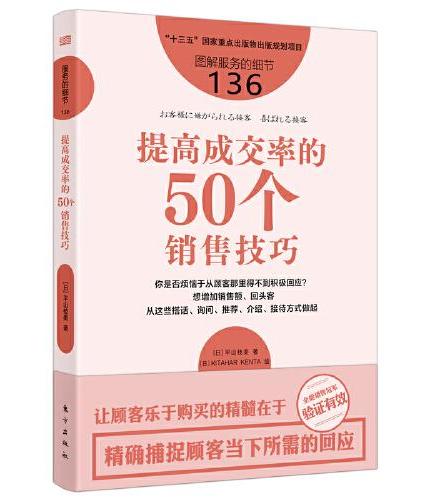
《
服务的细节136:提高成交率的50个销售技巧
》
售價:HK$
65.0

《
变法与党争:大明帝国的衰亡(1500—1644)
》
售價:HK$
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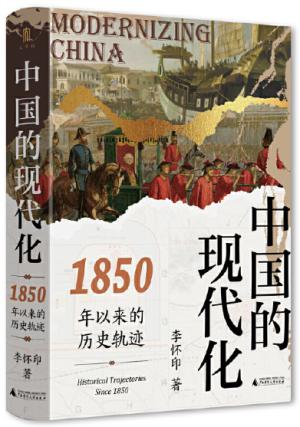
《
大学问·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
》
售價:HK$
105.0

《
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
》
售價:HK$
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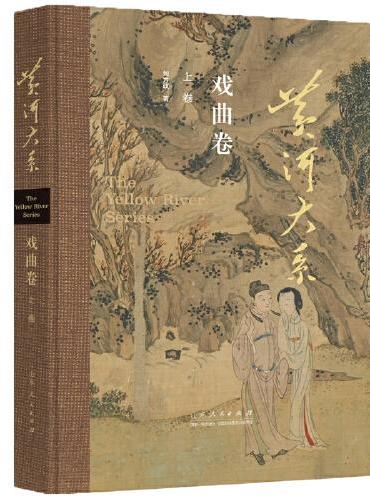
《
黄河大系?戏曲卷
》
售價:HK$
888.8
|
| 編輯推薦: |
总有一些话介于说了矫情,不说憋屈之中。
我们的声音越来越沉默,心却越来越孤独。
对一个失语者来说,最艰难的不是如何与人交流,而是如何让人倾听。
你站在这个世界里,你的思想在脑中不断划出一道道闪耀的光芒。但没人知道这一点,因为你是一个失语者。你无法告诉任何人,你无法说出你的感受,你无法让人们驻足听一听你的声音,人们似乎看不见你的存在,而你却不知道,为什么。
|
| 內容簡介: |
“我想让你们都停一下,真正思考一下没有声音,没有任何其他沟通方式的世界。”
——马丁·皮斯托留斯
当你醒来后,你已变成魂魄,但你还不知自己已经死了,怎么办?
每个人的身体,无非是一把无法逃脱的枷锁。
《失语者》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失语者》讲述了马丁历经十余年,在疾病与孤独的抗争中,如何表达出自己声音,和这个世界重建联系的感人故事。
12岁那年,马丁得了一种怪病,从此他失去了语言和行动能力,他试图与外界沟通,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人知道这个看似僵化的躯壳里藏着一个鲜活的灵魂。
每一次醒来,马丁都希望自己是漂在半空中的魂魄,这样就可以逃离身出捆绑他身体的这副枷锁。马丁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靠着幻想、聆听、观察这个世界,直到他开口说话的那一天……
|
| 關於作者: |
马丁·皮斯托留斯(Martin Pistorius)
1975年,马丁?皮斯托留斯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12岁那年,他患上一种未知疾病,无法说话,必须坐在轮椅上,在疗养院度过了14年。2001年,马丁通过电脑开始学习沟通,交朋友,改变自己的生活。2008年,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至爱乔安娜,并且移民去了英国。2009年他们结婚,2010年马丁开始自己创业。
马丁说自己是个怪胎,有恶作剧的幽默感,并且喜欢技术。他喜欢动物,喜欢摄影,喜欢看板球赛和F1赛车,喜欢看电影听音乐,喜欢和朋友在一起,而最最喜欢的,是和妻子在一起。
|
| 目錄:
|
楔子 希望之鸟
1 倒数开始
2 绝命深渊
3 行走在海面
4 囚笼之徒
5 维娜的呼唤
6 现在苏醒
7 爸爸和妈妈
8 蝴蝶效应
9 开始和结束
10 天天年年
11 孤独通道
12 生与死
13 我一定得死
14 想象的世界
15 主宰一个煎蛋
16 心碎的秘密
17 咬人的快乐
18 三大愤怒
19 孔雀的羽毛
20 敢于做梦
21 她的秘密
22 破茧的微笑
23 无法拒绝的邀请
24 一步之遥
25 海中的绝望
26 困兽梦靥
27 天秤座的聚会
28 他们的爱情
29 信仰治疗师
30 一辈子的安静
31 国王的演讲
32 看看这个世界
33 甩不掉的恐惧
34 潘多拉
35 回闪
36 黑暗的往事
37 无止境的逃脱
38 新朋友
39 它很快乐
40 爷爷和奶奶
41 永不消失的爱
42 我和我的世界
43 你好,陌生人
44 只若初见
45 迪士尼的约会
46 等待真我
47 狮子的心
48 无关逻辑与臆想
49 糖和盐
50 坠入生活
51 玻璃瓶的沙子
52 迟到的告别
53 回到伦敦
54 在一起
55 选择障碍
56 金格和佛瑞德
57 受伤的野兽
58 在路口
59 好消息的坦白
60 热气球
61 八岁的圣诞礼物
62 再见,失语者
63 等待
64 约
致谢
|
| 內容試閱:
|
楔子 希望之鸟
电视上又演《紫色小恐龙班尼》①了。我讨厌班尼和它的主题曲——它跟《扬基歌》②完全是同一个调子。
电视里,孩子们开心地跳到紫色大恐龙的怀里。我无聊地看了看四周,这房间里的孩子们都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或是瘫在椅子里。要不是有根带子绑着,我也会瘫在里面。从生理上来说,我和这些孩子一样,身体成为我无法逃脱的枷锁:我想说话,但嗓子发不出声音;我想挪一下胳膊,可这也是徒劳。
我同这些孩子只有一点区别:我的思想试图挣脱束缚,它既可以跳跃也可以俯冲,既可以前滚翻也可以侧翻,在灰色世界里划出一道闪耀的光芒。但没人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无法告诉任何人。他们都以为我空有一具躯壳,所以在过去的九年里,我只能日复一日地坐在这里看《紫色小恐龙班尼》或《狮子王》。我以为这已经够糟糕了,不料后来又出了《天线宝宝》。
我二十五岁了,但对过去的记忆仅始于苏醒的那一刻,之前的事情全都不记得了。黑暗中,我感到好像有几束光照来,然后就听到人们谈论我的十六岁生日,他们还在商量是否要把我下巴上的胡楂儿剃掉。听到他们说的话我很害怕,因为我虽然对过去没有记忆,也没有感觉,但很肯定我当时还是一个孩子,而他们谈论的却是一个半大的小伙子。我开始想起,每天晚上我都会见到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然后才慢慢发现他们说的就是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电影情节:一个人醒来后已经变成了魂魄,但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我当时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人们似乎看不见我,而我却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不管我试着怎么努力呼喊和恳求,都没有人注意我。我的灵魂被困在了一具无用的躯体里,手脚不听使唤,喉咙也发不出声音。我无法发出任何信号或声音让人们知道我其实已经恢复了意识。我只是个隐形人——一个灵魂而已。
因此,随着生命在一天天重复不变的日子里慢慢逝去,我学着将自己的秘密放在心里,默默地看着周围的世界。重获意识已有九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用自己唯一的所有——我的思想,来逃脱现实,体验了无尽绝望的痛苦和幻想奇境的美妙。
在遇到维娜之前,事情一直都是这样的。而至今只有她怀疑在我体内还隐藏着活跃的意识。维娜相信我对于事物的理解超乎任何人的想象。明天她会带我去一个专门的医疗中心,因唐氏综合征①、自闭症、脑肿瘤和中风而不能说话的患者,都可以在他们的帮助下进行交流。
我仍然有些不敢相信这会将我从躯壳深处释放出来。我的灵魂已经被深锁在躯体中——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接受了这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而现在,我的命运可能就此改变,我还真的有些不敢去想。但不管多么恐惧,当想到终于会有人意识到我的存在时,我感到希望之鸟开始在我心里张开羽翼。
1 倒数开始
每天我都待在护理中心。它位于南非一座大城市的郊区,几小时路程之外就是一座山,山上满是黄色灌木丛。狮子四处寻找猎物,土狼对其剩下的腐肉虎视眈眈,最后秃鹫也希望能从骨头上啄下最后几丝碎肉。没有任何浪费,动物王国这一完美的生死循环过程和时间一般永无止息。
对于时间的无限性我已了如指掌,而且已学会沉迷其中。无论是一天还是一个星期,我都可以闭上眼睛,沉下心来什么都不去想。这样他们每天就只是在给一具空洞的形骸洗澡、喂食,并且把他从轮椅上挪到床上。有时我也会专注于视线范围内这巴掌大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地面上蚂蚁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战争和冲突,一刻也不停歇。其血腥和残酷程度丝毫不输于任何人类的争斗历史,却只有我一个见证人。
我还学会了自己计算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时间。虽然很少看见时钟,但我从阳光和影子在周围的移动中学会了辨别时间,只要有人问时间,我都能记住那个时间点阳光落下时照在什么位置。在护理中心我有无尽的时间,我便用一些固定的时间点:早晨十点喝早茶,十一点半吃午餐,下午三点喝下午茶,将计算时间的技能练得炉火纯青——毕竟我有太多机会练习了。
这也就是说,现在的我可以直面每一天,用分钟或小时在心里倒计时。数字寂静的声音充满我的内心:一和四的发音绵长优美,二和八则短促有力。像这样消遣了一个星期后,我开始感激这儿的灿烂阳光。如果生在冰岛,我绝不可能会辨别时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每天就只能放任时间对我进行无休止地冲刷,像海滩上的卵石般一点点被腐蚀掉。
我知道冰岛有漫长的黑夜和短暂的白天,也知道土狼和秃鹫会先后去吃狮子吃剩的腐肉,但我也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因为没人给我上过课,或是读书给我听,只有每次当电视或收音机开着时,我才能沉浸于其中,如饥似渴地获得信息——那声音就像通往遍地黄金的彩虹路①,引领我走向外部世界。所以我想,是不是得病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疾病损害了我的身体,但对思想的损害却只是暂时的。
时间已过正午,也就是说不到五个小时后,爸爸就会来接我了。这是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因为下午五点他来了之后,我就不用待在护理中心了。有时妈妈工作结束得早,会在两点来接我,这时候,我简直无法形容自己有多激动。
我开始倒数了——一秒一秒,一分一分,一个小时——我希望这样数着,爸爸就能快点儿来接我。
1、2、3、4、5……
希望在回去的路上爸爸能打开收音机,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听板球赛了。
投球手击中三柱门时爸爸有时会大喊:“出局!”
弟弟打电脑游戏时也会很激动。有时他会飞快地按着手柄尖叫:“升级了!”
他们都不知道我多么珍惜这些时刻。如果击中了6分球,爸爸会欢呼雀跃;为了在游戏中得高分,弟弟常常会眉头紧锁。这个时候我会静静地设想,如果我能说话,我要说些什么笑话,或者和他们一起叫喊些什么。在这些难得的时刻,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旁观者。
我希望爸爸快来。
33、34、35……
今天我感觉身体很沉,身上绑着的那根带子透过衣服像刀割一般勒着我。右半边屁股好疼。要是有人能过来把我放平,让我躺下就好了。连续坐上几个小时,可一点儿都不像你想的那么轻松。动画片里经常会有人从山峰摔下,屁股着地——然后摔成碎片。我也有这种感觉,就好像我被摔成了几百万个碎片,每个碎片都疼得要死。可见当承受到无法承受的重量时,身体就会变得疼痛万分。
57、58、59,一分钟了。
还有四小时五十九分钟。
1、2、3、4、5……
虽然努力在数,可屁股上的疼痛仍在不停地折磨着我,使我无法专心。我想到了摔下山谷的卡通人物。有时真希望我能像他们一样摔在地上,屁股碎成几瓣。或许那时,我也会和他们一样奇迹般地跳起来,所有伤痛都立刻痊愈,然后又能跑跑跳跳了。
2 绝命深渊
十二岁之前,我是一个正常的小男孩。虽然可能比其他男孩更害羞一些,也没有他们那么调皮,可我一直开心健康地生活着。我最喜欢摆弄一些电子物件,并且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妈妈很信任我,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就让我修插座,那时我已有好多年自己连接电路的经验了。我还在爸妈电脑里装了一个重置键,在自己卧室里安了一套报警系统,让弟弟戴维和妹妹金进不去,他们都很想入侵我的乐高玩具小王国。但是除了爸妈之外,我只允许我们家的小黄狗波克进我的卧室——我到哪儿它都跟着我。
这些年来,我和别人有过无数次会面,每次我都会竖起耳朵聆听,所以获得了不少信息。例如,1988年1月,我一放学回到家就开始抱怨嗓子疼,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去上过学。随后的几个月,我不再吃饭,每天没日没夜地睡觉,一走路腿就特别疼。当我不再使用自己的身体时,它就开始变得虚弱;而我的大脑也是如此:开始我忘记了一些事情,后来我想不起来一些日常事务,如要给我的盆栽树浇水,最后,我连人都不认识了。
爸爸妈妈让我随身带着一个全家福相框,帮我记住家人。每天爸爸去上班,妈妈琼都会给我播放爸爸罗德尼的视频。他们希望能通过重复印象的方式帮助我记忆,但这根本没用。慢慢地,我忘了自己是谁,身在何处。而语言能力也在退化。一年后,我在医院病床上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啊?”
我的肌肉不再被使用,四肢开始痉挛,手脚像动物爪子一样向内蜷曲,并且丧失了一切记忆。我的体重直线下滑,为了不让我饿着,他们会叫醒我,喂我吃饭。爸爸扶着我,妈妈把食物用汤匙送到我嘴里,我全凭本能吞下去。除此之外,我一动不动,对什么都没反应。人虽然醒着,却处于昏迷状态中。没人知道为什么,医生也无法诊断出病因。
开始,内科医生认为我的病缘于心理,所以让我在精神病科看了几个星期。心理学家没能说服我吃东西或喝水,最后我还因为脱水被送到了急诊室。这时,他们才认可我的病是生理问题,而非心理问题。所以接下来他们又给我做了脑部断层扫描、脑电图、核磁共振成像和血液检验。然后他们把我当做结核病和隐球菌脑膜炎患者来治疗。但最后仍没有确切的诊断结果。大家也做了很多药物疗法的尝试:氯化镁和钾、两性霉素和氨西林,但都没有效果。我的病远非药物能够治疗。我像在恶龙的巢穴迷了路,没有人能救得了我。
爸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每天离他们远去:他们想让我走路,但因为我的腿变得越来越虚弱,我必须有人扶着才能走;他们带我去了南非所有的医院,作了无数次检查,最后仍没有结果;在绝望之中他们给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专家写信,但就连这些医疗专家也表示无能为力,因为南非的医生确实已经做了所有的努力。
一年后,医生们终于放弃,认为已找不出任何治疗方案。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我患的是退化性神经紊乱,病因和病情发展无从得知。他们建议爸妈把我送进护理机构,不再进行治疗。医疗专家们如实告诉他们,我只能等死了,而只有死亡才能让我们所有人都解脱——他们非常礼貌但又很坚决地拒绝再对我负任何责任。
因此爸妈把我带回家了。妈妈放弃了放射影像技师的工作,每天在家照顾我。爸爸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经常是他回到家戴维和金都已经睡着了。但总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大约过了一年后,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他们决定把我送到日间护理中心——也就是现在我待的这家护理中心,每天晚上他们接我回家。
接下来的几年,我的世界就是无边际的黑暗。爸妈甚至一度把床垫直接铺在起居室地板上,这样一家人就都和我一样地生活。他们希望这样能离我近一些。但我当时的身体只是一具空壳,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恢复意识。
3 行走在海面
我是在海底费力爬行的海洋生物。好黑,好冷,环绕我的只有黑暗。
但突然间头顶隐约有光在微微闪烁,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告诉我,一定要努力触摸到那闪烁的光。于是,我努力向上蹬脚,试图触摸到上面轻轻掠过的点点微光——水波起舞,光影变幻。
*
眼睛聚焦。看到踢脚线。我敢肯定这和平常的踢脚线不一样,但我也很纳闷自己是怎么知道的。
*
一抹轻柔掠过我的脸庞——是风。
*
闻到了阳光的芬芳。
*
音乐声忽高忽低。孩子们的歌声时近时远,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直到最后回归寂静。
*
视线里出现了一条毯子,我模糊地分辨出那是黑色、白色和棕色构成的一团图案。我盯着它,想看清到底是什么图案,但是眼前又变成了一片漆黑。
*
有湿布擦在脸上,凉凉的。一只手扶正我的脖子,我感到脸颊因为抗拒而发热。
“就一小会儿。”一个声音响起,“你是个干净的孩子,不是吗?”
*
那些光显得更亮了,离水面已越来越近。我想冲破水面,却做不到。万物都在动,我却动不了。
*
闻到一股什么气味。
我费力睁开沉重的双眼。
一个小女孩正站在我面前。她裸着下身,手上涂满了棕黄色,傻笑着要开门。
视线边缘出现一双腿,然后是一个声音:“你要去哪儿,小玛丽?”
然后就是关门的声音和因为恶心而发出的声音。
那个声音叫道:“下次别再让我碰到!看看我手上!”
小女孩大笑起来。她的兴奋像废弃海滩上的一阵海风,在平整的沙滩上留下一个个沟槽。我能感到内心因此而泛起的涟漪。
一个声音。有人在说话。两个关键词。十六岁,死亡。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
晚上醒来时发现我躺在自己床上——在家里。昏暗中,我凝视着自己的房间。身旁是一排泰迪熊,脚边也有东西——是波克。
一直缠绕身体的那种沉重感消失了,感觉自己好像在上升。我很困惑,因为这是现实,而不是在大海里。但我仍感到自己漂浮着,好像离开了身体,向卧室房顶飘去。
突然我意识到房间里并非只有我在。好多陌生面孔围在我身边。他们安慰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忽然明白,没有理由留下了。我一直努力想要触到海平面却总无法到达,太累了。我想放弃,就留在深海里,或者就随这些陌生面孔一起远去——随便哪一个。
但这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想法:我不能离开家人。
他们难过是因为我。每次冲破海面的波浪,他们的悲伤都将我围得密不透风。如果我走了他们的生活就没有了指望,我绝不能走。
一阵急促的呼吸,我睁开了眼。房间里又只剩我一个人了,刚才那些面孔全都消失了。
那是天使。
我决定要留下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