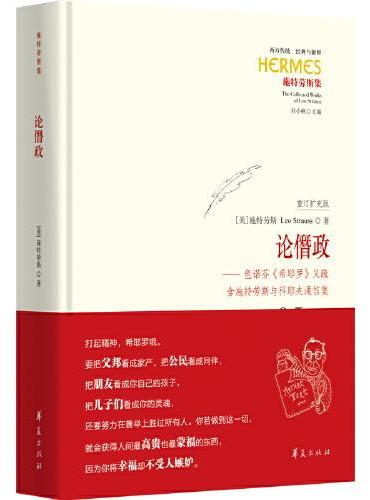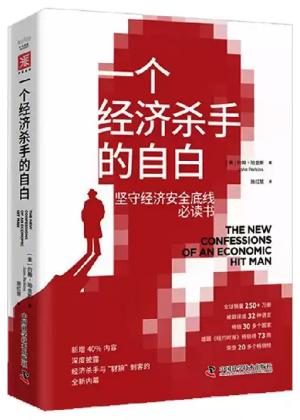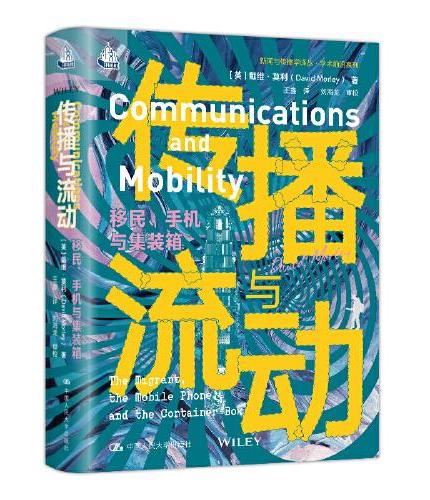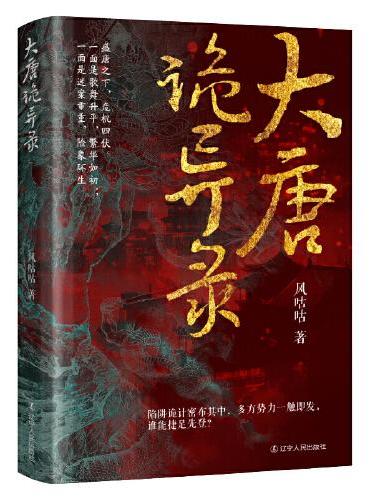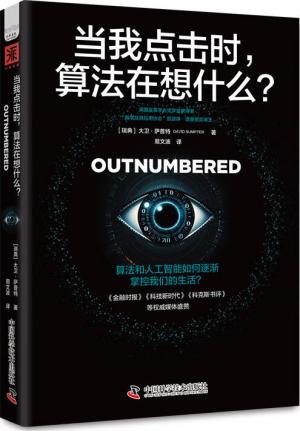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开宝九年
》
售價:HK$
54.9

《
摄影构图法则:让画面从无序到有序
》
售價:HK$
1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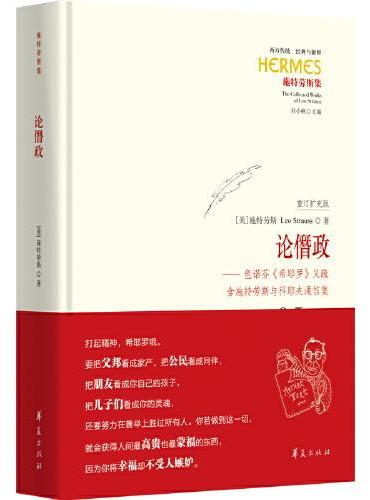
《
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含施特劳斯与科耶夫通信集)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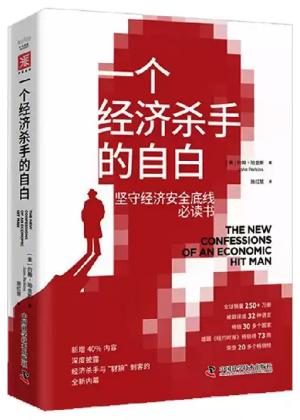
《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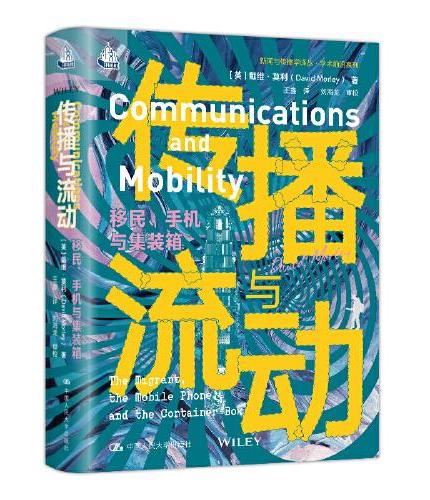
《
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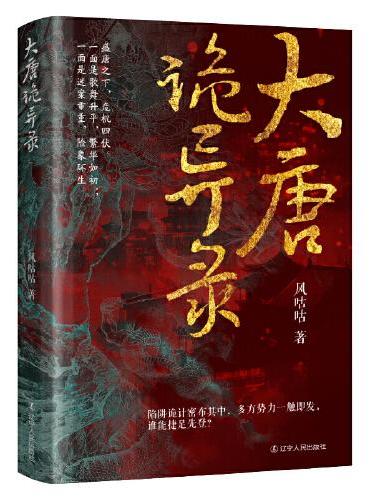
《
大唐诡异录
》
售價:HK$
55.8

《
《证券分析》前传:格雷厄姆投资思想与证券分析方法
》
售價:HK$
1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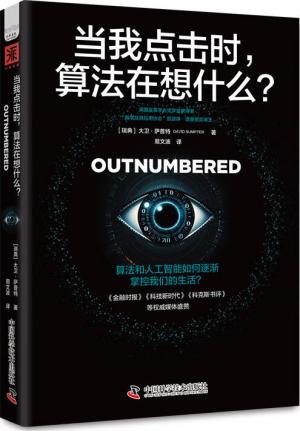
《
当我点击时,算法在想什么?
》
售價:HK$
78.2
|
| 編輯推薦: |
唯一能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战胜丹?布朗和J.K.罗琳的作家
比《达芬奇密码》更有艺术性,将自然、历史、科学完美融合在惊悚和悬疑之中
比007更神秘的超级特工潘德格斯特,领衔主演“博物馆惊悚三部曲”开篇之作
起印量超过四十万的惊悚推理小说!
|
| 內容簡介: |
|
深夜,著名艺术评论者杰里米?格罗夫惨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分不清被熔化还是被烧焦的尸体令人不忍卒睹,旁边那恐怖的印记更是让身经百战的警官们都屏住了呼吸。达戈斯塔警官参与了调查,更在案发现场遇到了自己多年的好友,超级特工潘德格斯特。两人又一次携手,这次的目标是挑战用人类的力量无法解释的超自然案件。可是,一个又一个的受害者出现,牵涉到的黑暗内幕也越来越多,更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慢慢逼近了他们……真相到底为何?魔鬼会不会被人类的英雄击败?看到最后,你才能得到答案。
|
| 關於作者: |
道格拉斯·普莱斯顿,美国畅销小说作家。他与比自己小一岁的搭档林肯·查尔德共同创作的“科技惊悚小说”在出版业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销量神话,被视为可以媲美“007”和“碟中谍”系列的超级娱乐现象。
大学时的普莱斯顿涉猎广泛,学习过数学、生物学、物理学、人类学、化学和天文学等领域的课程,最后才决定专攻英国文学。
一九八六年,刚满三十岁的道格拉斯·普莱斯顿告别居住了八年的纽约,驾车横穿美国,搬到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全心写作。在这之前,他任职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开始撰写一本名为《阁楼里的恐龙》的作品,介绍那些千奇百怪、大部分时间都被深锁在储藏室里不见天日的馆藏。
他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编辑一路做到出版统筹,既锻炼了笔锋,也增长了见识,为日后创作奠定了基础。迁居之后,普莱斯顿一边进行新书《寻找黄金城》的创作,一边开始构思一部以自然历史博物馆为背景的推理小说,并把写作提纲寄给《阁楼里的恐龙》的编辑林肯·查尔德。不过,看到提纲时,查尔德已经不在出版界工作了。
普莱斯顿和查尔德都毕业于英文系。查尔德对恐怖小说情有独钟,编过几本鬼故事精选,还是个自学成才的程序设计高手。收到提纲后,查尔德认为市面上的推理小说泛滥,不如改写科技惊悚小说(techno-thriller),并希望与普莱斯顿共同进行创作。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前博物馆员”加“前出版社编辑”的组合,会成为当代最受读者喜爱的黄金搭档。他们创作的每一本书,都能达到百万的销量,风靡世界几十个国家,这样的成绩,也许只有史蒂芬·金这样的大师才能与之媲美,而这两位搭档的创作之路,还在不断继续着。
|
| 內容試閱:
|
末日的仪式末日的仪式
(美)道格拉斯?普莱斯顿 林肯?查尔德 著
Brimstone
赵文伟 译
1
黎明时分,阿格尼丝?托雷斯把白色的福特护卫者停在篱笆墙外的小停车场里,然后迈步走进凉爽的空气中。篱笆高约十二英尺,犹如一面砖墙,无法穿越;站在大街上,只能望见这座大宅的木瓦屋顶。然而,在这里,她能听见惊涛拍岸的声音,还能闻到从大海上远远飘来的咸味。
阿格尼丝小心翼翼地锁上车——即使在这种社区,也要严加防范。她在一大串钥匙里翻来覆去地寻找,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那把,然后将它插进锁孔里。沉重的铁门向内旋开,一大片绿色的草坪展现在她眼前,长约三百码,一直延伸到海滩,两侧各有一座沙丘。门上的键盘闪烁着一盏红灯,她哆哆嗦嗦地输入了密码。在报警器响起之前,她只有三十秒钟的时间。有一次,她把钥匙掉在了地上,没来得及按密码,结果整个镇子都被她吵醒了,还招来了三辆警车。杰里米先生非常愤怒,她觉得他的嘴里几乎能喷出火焰。当时的情形实在糟透了。
阿格尼丝用拳头捶了一下最后的按钮,那盏灯变成了绿色。她长舒一口气,锁上门,停下脚步,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接着,她掏出念珠,把第一枚珠子虔诚地夹在指间。现在,她已经做好了准备,转过身,抬起有一点粗的腿,蹒跚地穿过草坪。她走得很慢,这样才能有足够的时间用西班牙语低声吟诵《天父我神》、《圣母经》和《圣三光荣经》。通常,走进格罗夫庄园的那一刻,她刚好念完十遍《玫瑰经》。
一座灰色的大宅隐约出现在眼前,尖顶上那扇孤零零的眉窗蹙着眉头,就像希腊神话中独眼巨人的眼睛。那双眼睛是黄色的,房子和天空则是铁灰色的。海鸥在天空盘旋,时常不安地尖叫几声。
阿格尼丝吃了一惊,她不记得那里从前亮过灯。早上七点,杰里米先生会在阁楼里做什么呢?平时他不到中午是不会起床的。
祈祷完毕,她把念珠放回原处,接着又用那双干了几十年家务的粗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她动作迅速,而且不需要思索。她本来不希望杰里米先生醒着。她喜欢在空房子里干活,如果他起来了,一切都将变得令人不快:她刚擦完地,他就把烟灰弹在上面;她刚洗完碗,水池里就又多出一堆盘子;他总是喜欢发表评论,没完没了地骂自己,骂电话另一边的人,骂报纸上的文章,然后发出刺耳的大笑。
他的声音就像一把生了锈的刀子,切割、挥砍着空气。他瘦骨嶙峋、卑鄙无耻、满身烟臭,中午还要喝几杯白兰地。他每日每夜随时随地都能款待那些鸡奸者。有一次,他曾经试图对她讲西班牙语,但很快就被她制止了。除了她的家人和朋友,没人跟她说西班牙语,而且,阿格尼丝?托雷斯的英语很不错。
另一方面,阿格尼丝这辈子为很多人工作过,杰里米先生给她的待遇很好。他付给她丰厚的薪水,而且总是按时付钱。他从不要求她晚上加班,从不改变她的时间安排,也从不指责她偷窃。很久以前有一次他曾经当着她的面亵渎上帝。她跟他谈了这件事,他极为谦恭地向她道了歉,而且再也没犯过类似的错误。
她走上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来到后门,将第二把钥匙插进锁孔。她又一次紧张地触摸键盘区,关闭内部警报器。
这座房子灰暗阴森,站在窗前可以眺望愤怒的大海和点缀着海藻的沙滩。海浪声似乎被什么东西闷住了,房子里很热,异乎寻常地热。
她用鼻子闻了闻。空气中有一股怪味,好像是油乎乎的烤肉在烤箱里放了太久。她蹒跚着走进厨房,厨房里没有人,盘子摞得很高。这个地方还是那么杂乱,到处堆满变了味的食物,不过,怪味不是从这里飘出来的。看来,昨天杰里米先生煮过鱼。她通常不在星期二打扫房子,但前一天晚上他一定举办了晚餐会。类似的派对简直数不胜数。劳动节[1]在一个月前就过了,但杰里米先生的周末聚会得到十一月才能结束。
她走进起居室,又用鼻子闻了闻——肯定是什么地方烹调着东西。而且,除了这股味道,还有别的味道,好像有人在玩火柴。
阿格尼丝?托雷斯心中隐隐生出一阵恐慌。她是昨天下午两点离开这里的,而直到现在这里都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除了那些几乎从烟灰缸里漫溢出来的烟蒂。餐柜上摆着空葡萄酒瓶子,脏盘子堆在水槽里,有人把软奶酪掉到地毯上,还在上面踩了一脚——和平常一样。
她扬起圆脸,又闻了闻。味道是从上面传来的。
她登上台阶,轻轻地走上楼,然后在楼梯拐角处又停下来闻了闻。她蹑手蹑脚地走过格罗夫的书房,又经过他的卧室,继续沿着走廊向前走,接着,她走上楼梯,来到三楼。这里的味道更浓,空气更闷更热。她试图打开那扇门,却发现门是锁着的。
她掏出钥匙串,叮叮当当地寻找这扇门的钥匙,终于,她把门打开了。圣母马利亚啊,这里的味道更糟。她登上未完工的陡峭台阶,每迈一步,都要歇歇患有关节炎的腿。到了顶端,她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宽敞的顶楼有一条很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有六间闲置的儿童房、一间游戏室、几间浴室,还有一个没装修完的阁楼,里面堆满了家具、盒子和讨厌的现代绘画作品。
她看见一道黄色的光从走廊尽头最后一间卧室的门缝里露了出来。
她试探着向前走了几步,停下来,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她的心跳得很厉害,但手里攥着的念珠让她知道自己是安全的。越是靠近那扇门,那种怪味就越浓烈。
她轻轻地敲了敲门,以免吵醒杰里米先生的客人——也许有人喝多了或生病了,正在那间屋子里睡觉。可是,没人回应。她抓住门把手,奇怪,怎么摸起来是温的。着火了吗?是不是有人睡着了,手里拿着烟?空气中的确有一股淡淡的烟味,但又不止是烟味;是一种更浓的味道,一股臭味。
她拧了一下门把手,结果,门锁着。这不禁让她回想起当年在教会学校读书,疯狂的老修女安娜死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破门而入。
里面那个人也许需要她的帮助;他可能病了,或者丧失了行动能力。她又开始摸索钥匙。她不知道该用哪把钥匙打开这扇门,所以差不多试到第十把,正确的钥匙才出现。她屏住呼吸,打开门,但门只动了一英寸,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她推呀推,使劲地推,接着,听到里面
传出砰的一声。
圣母马利亚,这会吵醒杰里米先生的。她等了一会儿,却没听见他的脚步声,也没有重重关浴室门的声音或是冲马桶的声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已经气急败坏地起床了。
她用力推门,门开了一道缝,宽度刚好允许她把头伸进去。她屏住呼吸,不让自己闻那个味道。一层薄薄的烟雾在房间里漂浮,屋里热得像个烤箱。这个房间已经封闭了很多年,杰里米先生讨厌小孩子,还讨厌掉皮的凹槽装壁板上那些肮脏的蜘蛛网。刚才之所以砰响了一声,是因为堵住门的老衣橱倒了。实际上,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除了床之外,好像都堆在门口。她看见床摆在房间的另一边,杰里米先生在上面和衣而卧。
“杰里米先生?”她轻轻呼唤了一声。
但阿格尼丝?托雷斯意识到自己不会得到回答了。杰里米先生没有睡觉,他烧焦的眼睛永远不可能再闭上,他布满灰尘的、圆锥形的嘴凝固成尖叫的姿态,发黑的舌头肿得像根西班牙香肠,旗杆一般直挺挺地从嘴里伸了出来。一个睡着的人不可能躺在那里,肘部扬在床的上方。他的拳头攥得太紧,血从指缝里渗了出来。一个睡着的人不可能躯干烧焦,像一块烧煳了的木头那样蜷缩成一团。小时候在哥伦比亚,她见过很多死人,而杰里米先生比任何死人都更像死人。
她听见有人在说话,后来意识到是自己在嘟哝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她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翻出那串念珠。可是,她的脚忽然动弹不得,视线也被钉在了房间里的这一幕上。地板上有一个烧焦的标志,就在床脚;阿格尼丝认识那个标志。
就在这一瞬间,她忽然明白杰里米?格罗夫先生出了什么事。
一声被压抑的尖叫冲出她的喉咙,突然涌出的能量推动她逃出了房间,然后关上门。她找出钥匙,重又把门锁起来,嘴里一直念叨着:“我信上帝,全能的天父,创造天地的主。”她一次又一次地在胸前画着十字,手里攥着念珠,把它举到胸口,一步一步沿着走廊向后退,啜泣中混杂着含糊的祈祷词。
烙在地板上的分瓣蹄印已经把她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她。魔鬼终于要了杰里米?格罗夫的命。
2
达戈斯塔停下手里的活儿,不再用黄色警戒带将案发现场围起来,他的眼神里带着偏见。场面本来就一团糟,而且注定会更糟。路障设置得太迟,看热闹的人已经占领了海滩和沙丘,还破坏了沙子保存的所有线索。路障也放错了地方,他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开,因为一对情侣的路虎揽胜被困在了里面。那两个人从车上下来,嚷嚷着要赴重要的约会(见发型师、打网球),他们挥舞着手机,扬言要给律师打电话。
背后传来讥笑声,告诉他这下子麻烦大了。这天是十月十六日,地点是长岛的南安普顿,这个镇子最臭名昭著的家伙被人杀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他听到布莱斯基警督的声音:“警司,你忘了那些篱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把整个犯罪现场围起来!”
警司没有理会他,开始把黄带子挂在格罗夫庄园四周的篱笆墙上。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想的,仿佛十二英尺高、藏着铁丝网的篱笆墙不足以阻挡记者,而塑料带子却可以办到似的。他看见了电视转播车,安装了卫星传输系统的汽车,远处还隐约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当地媒体的记者在沙丘路的路障旁聚成一堆,正在跟警察争论着什么。与此同时,后援小分队从沙格港和东汉普顿赶来了,一起来的还有南福克的重案组。警督把新来的人安排在海滩和沙丘沿线,徒劳地警告群众不要靠近。特别任务小组的小伙子们也来了,警司目送他们手提金属取证箱走进那栋房子。他本来可以和他们共事,甚至领导他们,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别的地方。
他继续在篱笆墙上挂带子,一直挂到海滩边的沙丘上,几个警察正在那里阻止好奇者上前。这群人其实很听话,他们只是像愚蠢的动物般盯着这座有着尖顶、角楼和滑稽窗户的叠瓦大宅。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场派对。有的人打开扬声器,一些壮小伙子噼噼啪啪地开启了啤酒瓶盖。在这异常炎热的秋老虎天气里,人们穿着短裤或泳裤,仿佛在抗拒夏天的结束。警司不由得暗自嘲笑他们,心想,如果这么喝啤酒吃薯条,不知道二十年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变成他这种身材。
他向后瞥了一眼那栋房子,看到特别行动小组的小伙子们正在草坪上匍匐前进,警督在一旁大踏步地走过。那个男人还没有找到线索。警司又感到一阵痛心,他在这里牵制人群,他的才华和受过的训练都白费了。他本应该在别处做一名真正的警察。
不过现在想这个也没用。
电视转播车上的东西已经卸下来了,摄像机架成一排,对准了拍摄大宅的最佳角度。与此同时,魅力十足的记者们开始对着麦克风抱怨。你也许不知道,布莱斯基警督已经离开了特别行动小组,正苍蝇扑食一般朝着这些摄像机狂奔过来。
警司摇了摇头。简直难以置信。
这时,他看到一个男人猫着腰穿过沙丘,东躲西藏地迂回前行。警司跟在那人身后,在草坪边上截住了他。他是一个摄影师,警司赶上他的时候,他已经跪在地上,用简直和大象的那个地方一样长的长焦镜头对准了来调查谋杀案的东汉普顿侦探们,那些侦探正站在阳台上向一位女仆问话。
警司把一只手放在镜头上,轻轻把它扭到一边。
“出去。”
“警官,拜托,求你了——”
“你不希望我没收你的胶卷吧?”警司仁慈地回答。他总是对尽职尽责的人抱有恻隐之心,即使他们是记者。
那个男人站起身,走了几步路,回头又拍了最后一张照片,接着便急匆匆地跑掉了。警司又向那栋房子走去,他顺着风走向那个凌乱的老地方,空气中有一股怪味,好像是烟火之类的。他发现电视摄像机围成了一个半圆,警督正站在中间,享受着人生的高潮。布莱斯基计划在下次选举时当上局长,此刻,现任局长正在度假,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机会了。你看他那个样子,简直像是自己杀了人。
为了避开特别行动小组,警司从草坪后面绕过,从池塘和喷泉背后抄了一条近路。当他靠近一段篱笆墙时,发现远处有一个男人正站在池塘边向水里扔面包屑喂鸭子。他打扮得像个游客,穿着很俗气:夏威夷风格的衬衫,欧克利[2]太阳镜,还有松松垮垮的大短裤。尽管夏天在一个月前就结束了,但对这个男人来说,好像这是在漫长严寒的冬季结束后,第一次站在阳光下。警司虽然对尽职尽责的摄影师和记者心怀同情,但绝对无法容忍游客出现在这种地方。游客是这个地球上的渣滓。
“喂,你!”
那个男人抬起头。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不知道这里是犯罪现场吗?”
“是,长官,非常抱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