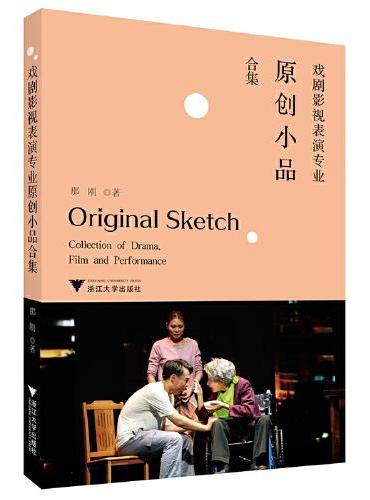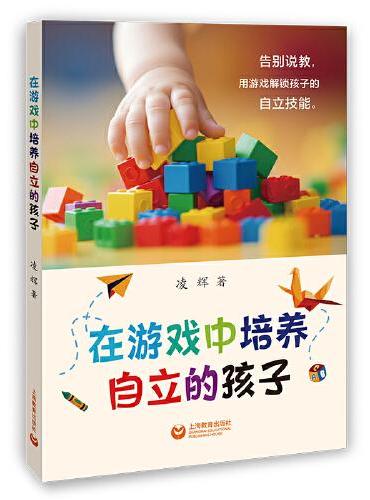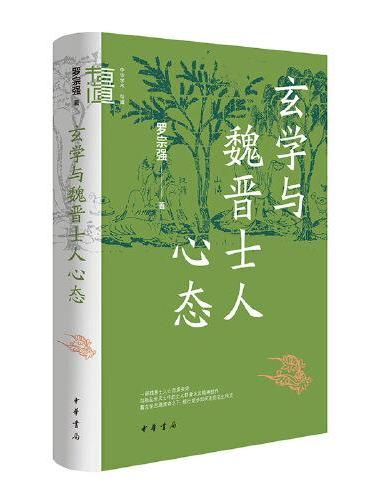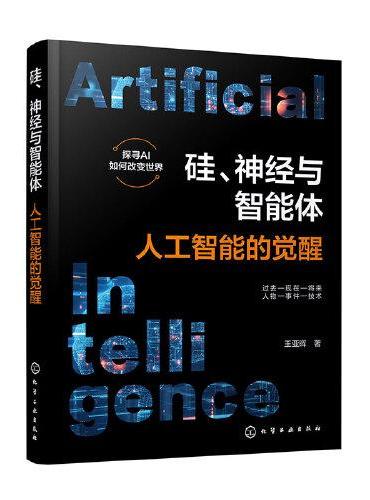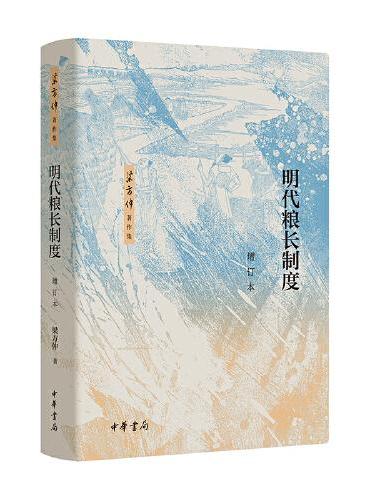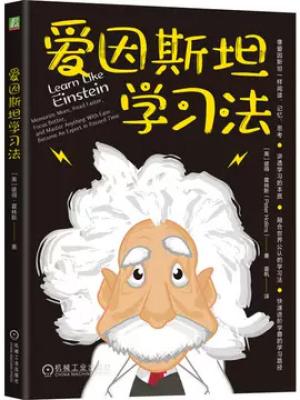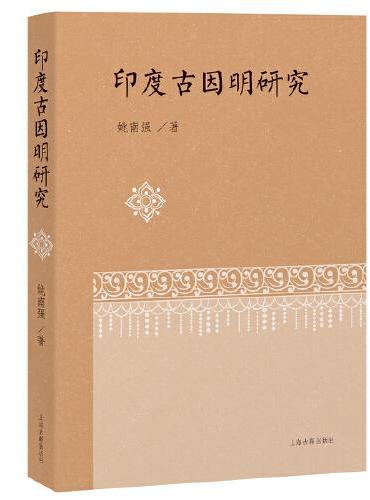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原创小品合集
》 售價:HK$
96.8
《
在游戏中培养自立的孩子
》 售價:HK$
49.5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85.8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HK$
85.8
《
明代粮长制度(增订本)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68.2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精选集
》 售價:HK$
85.8
《
爱因斯坦学习法
》 售價:HK$
60.5
《
印度古因明研究
》 售價:HK$
129.8
編輯推薦:
一部拆解民族记忆架构、挑战以色列禁忌、引发国际社会激辩的历史著作
內容簡介:
在现代,为了筹划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中存在着关联……是记忆的代言者们的努力工作发明了它。
關於作者:
施罗默·桑德作者
目錄
英文版序言
內容試閱
英文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