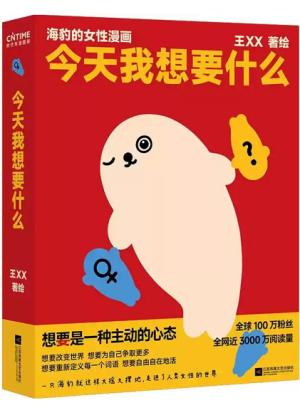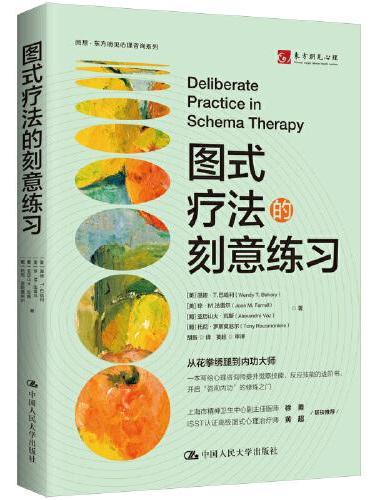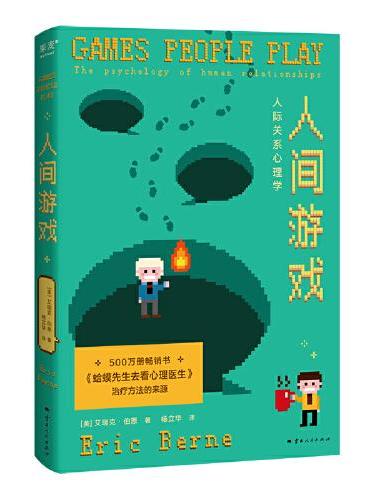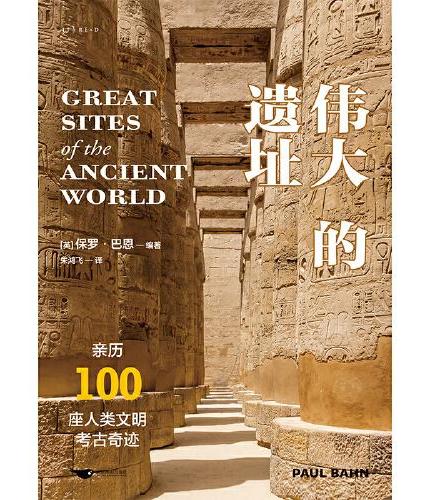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107.8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HK$
3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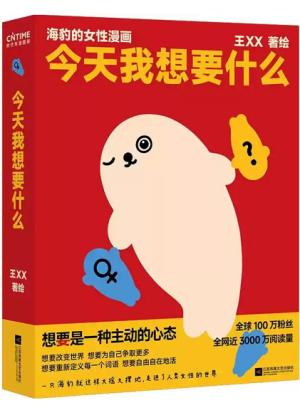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HK$
74.8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HK$
74.8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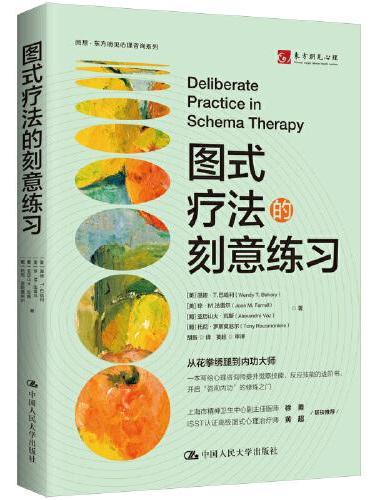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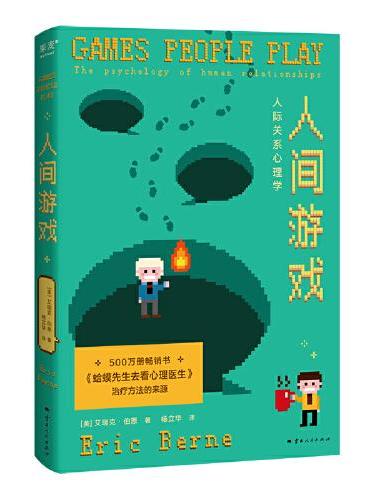
《
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500万册畅销书《蛤蟆先生》理论原典,帮你读懂人际关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
售價:HK$
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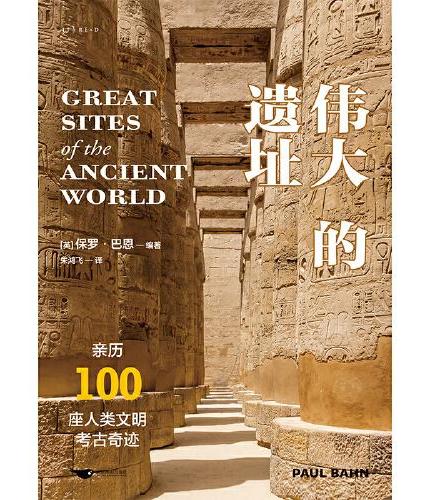
《
伟大的遗址(亲历100座人类文明考古奇迹)
》
售價:HK$
206.8
|
| 編輯推薦: |
◆ 很少有人在起床时就说:“嘿,我今天要犯罪。”但,每个人都可能随时犯下罪行。
◆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批评官员的尺度》译者何帆 作序推荐!
◆ 雄踞德国畅销书排行榜长达2年
◆ 德国克莱斯特文学奖;《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
◆ 《纽约时报》《明镜周刊》《镜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独立报》等重量级媒体 强力推荐!!
◆拍案推荐
作家 慕容雪村、梁文道、马家辉、蔡骏、孔二狗
学者止庵、何力、严蓓雯、李剑……
电影人彭浩翔、吴念真、唐骏、孙健敏、曾宝仪
法学家胡朝新;法学博士任羽中、林志毅
法官何帆、金轶;检察官云强、张国柱;律师王韵、周研……
◆每个淡然述说的故事背后,都是一个巨浪滔天的人生。
谁想犯罪?谁才是受害人?
无可奈何的罪行,又当如何判决?
作家、法官、检察官、律师、教授、白领、爱书人……一致拍案称奇!
|
| 內容簡介: |
德高望重的医生斧劈发妻,竟是出于对爱情的承诺与守护;
姐姐和弟弟相依为命多年,却亲手将弟弟溺死浴缸;
男子光天化日下连续抢劫银行,居然令参审人员当庭泪下……
……
11桩骇人听闻的案例,11次出人意料的判决,
撼动你对人性、对罪行、对爱与罚的全部判断!
我写的是一些关于谋杀、贩毒、抢劫银行和妓女的故事,他们各有各的遭遇,他们与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冯?席拉赫
|
| 關於作者: |
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1964年生于慕尼黑。1994年起至今担任执业律师,专司刑事案件。其委托人包括当时的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德意志联邦情报局特务诺贝特?尤雷茨科,以及工业巨头、知名人士和社会平民等。
2009年,出版处女作《罪行》,立刻引起巨大反响,登上《镜报》、《明镜周刊》等众多畅销书榜首,销量迅速超过50万册。
2010年以本书获选《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同年获颁德国文坛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
本书售出32国版权,同名电影即将由《香水》出品公司推出。
|
| 目錄:
|
序:有故事的人
前言
费内尔
正当防卫
棚田家族的茶碗
大提琴
刺猬
幸福
夏令时
绿色
拔刺的男孩
痴爱
埃塞俄比亚人
|
| 內容試閱:
|
弗莱德海姆?费内尔在罗特韦尔当了一辈子大夫,每年要开两千八百份病假证明,拥有一个临街的诊所,是埃及文化研究界的领头人,国际狮子会成员。他没有犯罪记录,甚至不曾违规。除了自住房,他还拥有两栋用于出租的房子,一辆三年前买的E级奔驰轿车,车内全真皮装饰,并安装了自动空调;持有价值七十五万欧元左右的股票、债券和一份寿险。费内尔没有要孩子,唯一的亲属是比他小六岁的妹妹,眼下与丈夫和两个孩子生活在斯图加特。费内尔的生活里原没什么故事好讲的。
直到他遇上英格里德。
二十四岁那年,费内尔在父亲六十岁的庆生宴上,认识了英格里德。费内尔的父亲也曾是罗特韦尔的大夫。
罗特韦尔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城市,到这儿的陌生人都能
看出这一点。这座城市是斯陶芬人建立的,也是巴登符腾堡州最古老的城市,随处可见中世纪风格的挑廊和十六世纪雕刻精美的牌匾。费内尔家族是本城的第一批居民,世代生活于此,家族成员行医、当法官和药剂师等,个个受人尊敬。
弗莱德海姆 ?费内尔长得像约翰
?肯尼迪,面容友善,无忧无虑,事事都能让他乐在其中。可要细看,却会从他脸上觉察到一丝忧伤和沉闷。不过在黑森和施瓦本山区许多人都这样。
英格里德的父母是罗特韦尔的药剂师,带着英格里德参加了费内尔父亲的那次庆生宴。她比费内尔大三岁,乌亮的头发、洁白的皮肤、水汪汪的蓝眼睛、丰满而坚挺的胸脯,是当地出了名的大美人。她也清楚自己的靓丽外表能迷倒一大片。她的嗓音如金属般铿锵,讲话时总是一个声调,这让费内尔稍觉不舒服,只有轻声说话时,她的语调才有起伏。
她中学没读完就去做餐馆招待了。“暂时的。”她这么对费内尔说,对此他倒无所谓。他感兴趣的是她身上散发的其他东西。在这之前,他只与两个女人有过短暂的交往,跟她们相处时总觉得不自在。可一看见英格里德,他就爱上了她。
寿宴后的第三天他们俩出去郊游,野餐结束后她开始引诱他。他们躺在一个避雨小屋里,英格里德是位床笫高手,弄得费内尔神魂颠倒,一周后就向她求婚了。她丝毫没犹豫就答应了他,因为费内尔正是人们所谓的“好郎君”。他当时还在慕尼黑攻读医学,即将参加毕业考试。他魅力十足、有亲和力,那股严肃认真的劲儿又最让她着迷。她曾对女朋友说过,她莫名地觉得费内尔一辈子也不会抛弃她。四个月之后,她搬过来与他同居了。
他们依着他的意愿,去开罗旅行结婚。事后被问及埃及之行如何时,他会回答“飘”。其实他知道别人听不懂,但还是这么说。那时的他就像年轻的帕西法尔,一个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呆瓜。这也是他这一生最后一次体验幸福。
返程的前一晚,他们躺在旅馆的房间里。窗户敞开着,闷热却不散去,小小的房间好像被空气塞得太满了似的。这是一家廉价的旅馆,有一股烂水果的味道,楼下街道上的噪音清晰可闻。
虽然天很热,他们还是做了爱。
事后,费内尔仰面躺着,凝视着天花板上的吊扇,英格里德躺在一旁抽烟。她转过身来,头枕在一条胳膊上盯着费内尔。他冲她笑了笑,而她却一言不发。
良久,她开口了。她给费内尔讲那些与她有过关系的男人,讲她的失望和过错。讲得最多的是那个让她怀孕的法国中尉,说那次
堕胎差点要了她的命,然后哭了起来。他惊慌失措地将她搂在怀里,胸膛感受着她的心跳,觉得爱莫能助。这是她对我毫无保留的信赖吧,他这么想着。
“你向我发誓,一辈子照顾我,不会抛弃我。”她的声音微颤。这着实打动了他,于是一个劲地安慰她说:“我在教堂举行婚礼时都发过誓了,我也说过和你在一起很幸福,我会
—”她粗暴地打断了他,用那高亢单调又刺耳的嗓门吼道:“你给我发誓!”
他恍然意识到,这不是情人之间会有的对话。头顶上的吊扇,开罗、金字塔、闷热的旅馆房间
—所有的一切突然都蒸发了,不见了。他把她往外推了推,四目相望,然后他才慢慢地开口,而且明了自己说的是什么:“我发誓。 ”
他重又把她搂在怀里,亲她的脸。
他们又开始做爱了,但这次的感觉却完全变了味。她骑在他身上,随心所欲。两人都很投入,但又觉得陌生和孤独。高潮来时,她抽了他好几个耳光。完事后,他久久不能入眠,盯着天花板发呆。停电了,吊扇不转了。
费内尔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了博士学位,在罗特韦尔县医院谋得了第一份工作。小两口找了一套带浴室的三室住房,可以望见不远处的森林。
在慕尼黑整理搬家时,她把他收藏的唱片全扔了,直到搬进新房后他才发现。她说自己无法忍受他与别的女人一起听过的唱片。他听了火冒三丈,之后两天谁也没搭理谁。
费内尔喜欢包豪斯的装修风格,简洁明快。可她却用橡木和松木装饰房间,再挂上厚厚的窗帘,铺上色彩艳丽的床单,添置绣花碗垫和锡质酒杯,所有这些他都忍受了,懒得去争。
几周后,英格里德说看不惯他拿餐刀的样子。起初他只是一笑了之,觉得她是在耍孩子气。可第二天、第三天,她还就此事喋喋不休。既然她看得这么重,他也只好改变了拿餐刀的方式。
英格里德抱怨他去上班时不把垃圾带下楼去。他就跟自己说,没事的,两人刚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但不久她又抱怨他下班回家太晚,说他肯定在外面有女人。
埋怨越来越多,天天不绝于耳。什么邋遢、弄脏了衬衣、弄皱了报纸、浑身一股怪味、只想自己那点事、净说废话、欺骗她……费内尔几乎从不辩解。
几年后,抱怨变成了破口大骂。开始还有所收敛,后来变本加厉。什么你是头猪、就知道折磨我、你是个蠢货……渐渐变得不堪入耳,简直成了泼妇骂街。他放弃了,不作任何反抗,得了闲就看科幻小说,像学生时代那样每天慢跑一小时。他们好长时间不做爱了。他虽然接受其他女人,但从来没有绯闻。三十五岁接管了父亲的诊所,
四十岁头发花白。他觉得累了。
费内尔四十八岁时,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也走了。他用父母的遗产在郊区买了一幢木结构的房子,房子附带一个小花园,里面灌木自生自灭,有四十棵苹果,十二棵板栗和一个小池塘。花园成了费内尔的大救星。他邮购图书,订购专业杂志,遍读园艺书籍,置办了最好的园林工具,研究浇灌技术,只要与园子有关,他都会倾力去琢磨透彻。在他的精心照料下,花园一片枝繁叶茂,竟也在这一带小有名气。费内尔甚至看见有陌生人在他的苹果园前照相留念。
上班日费内尔都在诊所里待很长时间。作为医生,他细致认真,富有同情心,获得了患者的一致信任。他的处方也成了罗特韦尔的标准处方。每天早上他都趁英格里德醒来之前离开家,晚上九点左右后才回去,在她喋喋不休的数落声中一声不吭地用完晚餐,无一日例外。英格里德的嗓音还是那金属般的一个声调,骂起来连珠炮似的咄咄逼人。她身材已经发胖,肌肤也由洁白转变成粉色,脖子上的皮肉也已松弛,喉咙前的赘肉还随着骂人的节奏不停地颤动,呼吸变得有些困难,并患上了高血压。费内尔却越来越瘦。一天晚上,费内尔听她骂了半天后,就劝她去一位神经科医生的朋友那儿瞧瞧,却被她一面吼骂成一头不负责任的猪,一面抄锅砸来。
六十周岁生日的前一晚,费内尔失眠了。他把埃及旅行结婚时拍的照片找了出来,照片都已退色:那是英格里德与他在胡夫金字塔前的合影,背景是骆驼、游客和黄沙。这本相册当时她扔了,是他从垃圾桶里把这张照片拾回来的。自那以后,他一直把它深藏在大衣柜里。
那晚他终于明白,他这一辈子,直到生命尽头,只是囚徒一个。他曾在开罗许下诺言,共享福贵,也同过难熬的日子。眼前的照片变得模糊起来。他脱光衣服站在浴室的镜子前,久久地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坐在浴缸沿上,长大成人后第一次伤心地哭了。
这一年费内尔已七十二岁,四年前他把诊所卖了。九月的那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六点起床,悄悄离开那间他长期以来单独睡的客房。英格里德还在酣睡。
外面阳光明媚,晨雾已经散去,空气清凉。他开始在花园里忙碌,给灌木丛锄草。这活儿不轻松,而且枯燥乏味,不过他还是觉得很惬意。他想着等到了九点半,就好好歇歇,美美地品味一杯浓香的咖啡,于是顿时觉得满怀愉悦。他还想那棵年初种下的翠雀花,到晚秋就要第三次开花了吧。
突然,他听见英格里德拉开阳台门,冲着他大喊:“你这个白痴,又忘了关上房间的窗户。”她的嗓音异常刺耳,像刮蹭光滑金属时发出的声响。
费内尔后来也无法准确描述当时的想法,只是觉得内心深处闪过一道凛冽锐利的光芒,在这道亮光下什么都变得一目了然。
他请求英格里德去地窖,自己则从屋外的楼梯先进去了。英格里德跟着气喘吁吁地赶到。这是他存放园艺工具的地方,所有物件都分门别类地或挂在墙上,或清洗后放在白铁桶和塑料桶里。工具都很考究,是他几年的专门积累。英格里德鲜少来这儿。她开门后,费内尔一声不吭地从墙上取下砍树用的斧头
—一把瑞典产的纯手工斧子,上过一层油,一点儿锈也没有。英格里德一时惊呆了。他当时还带着粗糙的园林手套。她则双目盯着那把斧头,没有躲避。第一斧子就是致命的,劈开了头颅,砍进了脑颅,将整个脸劈成两半。她在倒地之前就死了。费内尔一脚踩住她的脖子,费了好大劲才把斧子拔出来,再用力砍了两次将她的脑袋砍下。后经法医鉴定,她的手和脚他一共砍了十七斧子才卸下。
费内尔感到呼吸困难。他坐到一条平时种花草时用的小板凳上,凳脚泡在血泊中。他觉得饿了。不知过了多久,他在尸体旁脱掉衣服,在地窖的洗手池中把头发上和脸上的血迹洗掉,然后锁上地窖,从屋里的楼梯回到房间,上楼穿上衣服,拨了警察局的电话,报上姓
名和住址,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我把英格里德劈死了,快派人过来吧。”通话被记录在案。没等对方答话,他就把电话挂了。声音里没有一丝惊慌。
几分钟后,没拉响警笛也没亮警灯的警车来到费内尔家门口。其中有位警察在当地警察局干了二十九年,全家人都在费内尔那儿看过病。费内尔站在花园门口,把钥匙给了这位警察,告诉他,她在地窖里。那位警察知道,还是什么都别问更好:费内尔穿了一身西服,却没穿鞋和袜子,看上去异常镇静。
整个诉讼程序用了四天。陪审法庭的审判长阅历丰富,认识被告费内尔,也认识英格里德。即使他对他们不是很了解,证人们提供的证词也足够说明问题。所有人都为费内尔感到遗憾,都同情他。邮递员说,他把费内尔看作“一位圣人”,“他能容忍那个婆娘,简直是个奇迹”。心理医生的结论是:“情感淤塞”,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检察官要求判处费内尔八年徒刑。他不慌不忙地描述犯罪过程,让人联想地窖里的血腥场面。末了他说,费内尔是有选择的,他可以离婚。
不!检察官错了,恰恰是这一点费内尔无法做到。《刑事诉讼法》最新修正案中,废除了刑事诉讼中强制对供词真实性进行保证的宣誓规定。早就没有人相信誓言了。如果证人撒谎,那就让他撒吧。没有哪位法官会认为,有什么会因为誓言而改变。现代人已经把誓言这东西看得很淡了。
然而,正是在这个“然而”里,还有另一个世界。费内尔不是什么现代人,他对誓言是认真的。那个誓言与他的一生紧紧相连,甚至让他成了囚徒。费内尔不可能选择离婚,他认为那是一种背叛。因为那个誓言,他一辈子被束缚在一个压力罐里,现在这个压力罐实在承受不了了,被胀破了,酿成了惨案。
我是应费内尔妹妹的请求担任辩护律师的。她此刻坐在观众席上,一个劲地哭泣。费内尔当年诊所的护士握着她的手,不停地安慰她。费内尔则一动不动地坐在深色木板做成的被告席上。经过几天监禁,他越发显得瘦小。
其实这个案子并没有什么好辩护的,它只是一个法律哲学层面上的问题:惩罚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惩罚?我试图在最后的辩护陈述中寻找答案。当然,这方面的理论多如牛毛。惩罚应该有震慑、保护大众、阻止罪犯再度犯案,以及主持公道的作用。我们的法律集这些理论于一体,当中却没有一个适用于这个案子。费内尔不会再去杀人,他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是不争的事实,但却难以量刑。有谁会去报复他吗?
我用了相当长时间作最后的辩护陈述,我之所以讲他的故事,是想让大家知道,费内尔是因为身心疲惫,走到了尽头。直到感觉已说服当庭所有的人,我才结束了辩护。一位陪审员朝我点了点头,我才回到座位上坐下。
诉讼的最后程序是由法庭听取被告的陈述,法官要将这些陈述一并纳入庭议的内容。费内尔要作最后的陈述。他合抱双手向大家鞠躬。这一陈述他根本不用刻意去背诵,因为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爱我的夫人,但最终却把她杀了。直到现在我还爱着她,因为我曾向她发过誓,爱她一辈子。她还是我的夫人,这一点直到我的生命终点也不会改变。我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我将背负着这份罪孽,终了余生。
”
费内尔坐下,不再言语,盯着地板发呆。大厅里鸦雀无声,连庭长都感到一丝压抑。良久,他才宣布休庭,次日宣判。
这天晚上我再次到监狱探访了费内尔,其实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他从一个发皱的信封里取出了一张旅行结婚时拍的照片,用大拇指触摸着照片中英格里德的脸。照片的表层保护膜早被磨去,她的脸都已变成白色一片。
费内尔被判了三年徒刑,逮捕令被撤销,对他的羁押也结束了。他可以在开放式监狱服刑,也就是说过夜必须在监狱,但白天可以
自由外出,条件是他必须从事一项工作。可以他七十二岁的年纪,要找一份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后还是他妹妹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让他申请了卖水果的营业执照:出售自己果园里的苹果。
四个月后我在事务所收到一个邮件包裹,里面有十个红苹果,随附的信封里只有一张纸,上面写道:今年的苹果很好,费内尔。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