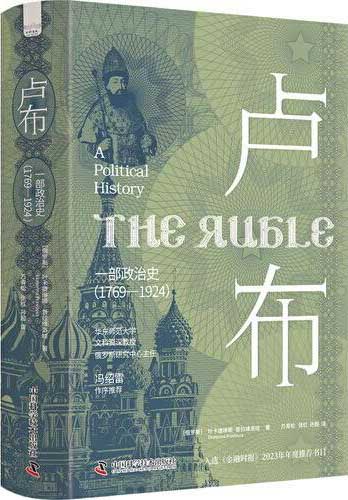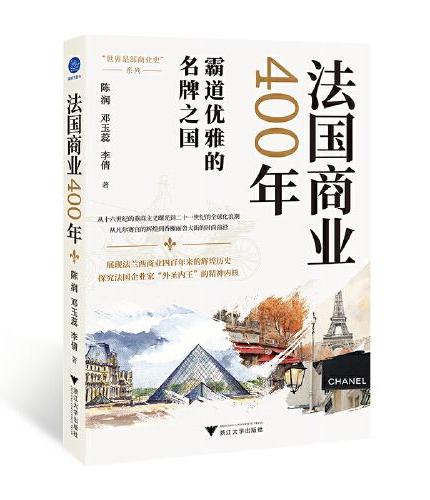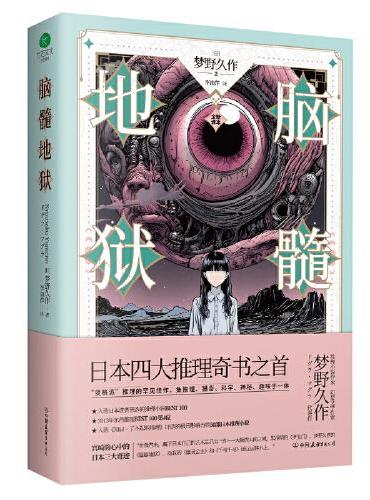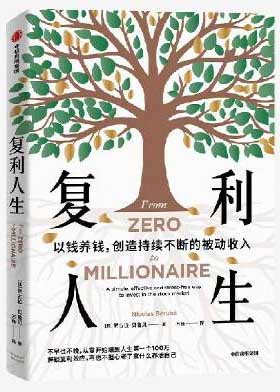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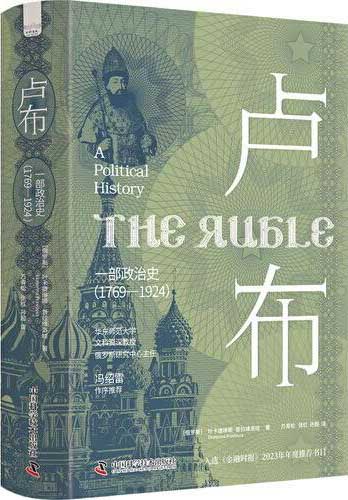
《
卢布:一部政治史 (1769—1924)(透过货币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兴衰二百年!俄罗斯历史研究参考读物!)
》
售價:HK$
1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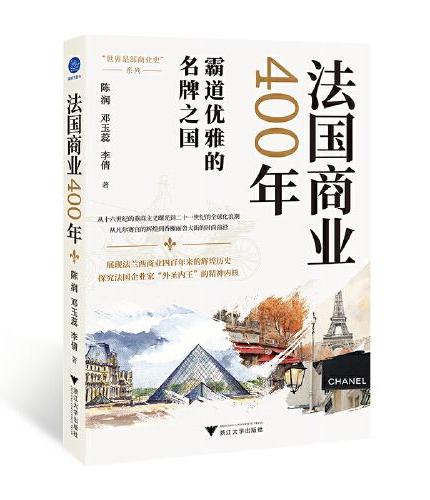
《
法国商业400年(展现法兰西商业四百年来的辉煌变迁,探究法国企业家“外圣内王”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74.8

《
机器人之梦:智能机器时代的人类未来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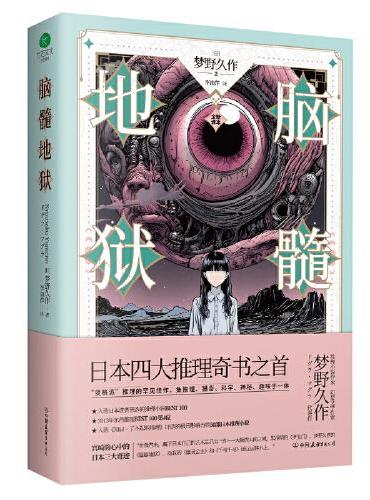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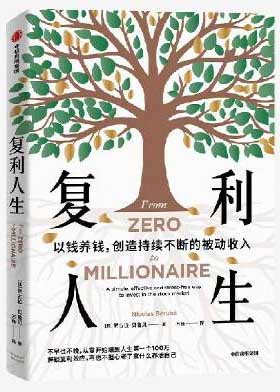
《
复利人生
》
售價:HK$
75.9

《
中国绘画:元至清(巫鸿“中国绘画”系列收官之作,重新理解中国绘画史)
》
售價:HK$
184.8

《
这里,群星闪耀:乒坛典藏·绽放巴黎(全套7册)
》
售價:HK$
259.6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HK$
60.5
|
| 編輯推薦: |
他坚韧,不吝惜人生;他坚韧,不吝惜自己
自他之后,再没有人像他这样写作
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文坛硬汉”创作生涯里的罕见长篇
四十万字写就的三天心灵史,海明威的二战记忆
|
| 內容簡介: |
|
1936年初秋到1939年春的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线的序幕,也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和德意法西斯政权之间的第一次较量。这部小说即以此为题材写作而成。这是海明威篇幅最大的一部小说,但全书情节局限于三天之内(1937年5月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二上午),写得紧凑非凡。海明威发挥他独特的叙事艺术,以细致入微的动作描写及丰富多彩的对白,一气呵成地把这故事讲到底,是部异常精彩的小说。
|
| 關於作者: |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之后创作不辍,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永别了,武器》(1929)、《丧钟为谁而鸣》(1940)等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褐色的地面上积着一层松针,他双臂交叉紧贴地面,下巴垫在上面屏息凝神,头顶上空,风从松树梢上呼啸而过。他俯躺着的山坡坡度不大,再往下却陡峭得很,他看见一条黑色的柏油路蜿蜒穿过山口。沿着柏油路有条小河,山口远处的河岸上有家锯木厂,拦水坝泄出的河水在夏天的烈日下就像一条白练。
“那就是锯木厂么?”他问。
“是的。”
“我记不得了。”
“你在这时还没建成。老锯木厂还在前面,离山口很远。”
他把影印的军用地图摊开摆在地上,仔细端详。老头儿从他肩后看着。这个老头儿虽矮却很结实,身穿一件农民的黑罩衫和一条硬邦邦的灰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他因为爬山而累得气喘吁吁,一手搁在他们带来的两只沉背包的之中一只上面。
“这么说从这里是看不到那座桥了。”
“看不到,”老头儿说。“山口这一带地势平坦,水流不急。再往前,就在公路拐进林子不见踪影的地方,地势陡降,那里有个很深的峡谷——”
“我记得。”
“那座桥就横架在峡谷上面。”
“他们的哨所在哪儿?”
“有个哨所就在你看到的锯木厂那边。”
这个正在研究地形的年轻人,从他褪了色的卡其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调校焦距,直到目镜中的景象突然清晰起来,他看到了锯木厂的木板,还看到了门边的一条长板凳;还有敞棚里的圆锯,以及敞棚后面的一大堆木屑;他还看到一段把河对岸山坡上的木料运下来的水槽。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清澈而平静,水坝泻下来的河水打着漩涡卷起滚滚飞沫,底下的浪花在风中飞溅。
“没有哨兵。”
“锯木房里在冒烟,”老头儿说。“还晾着几件衣服。”
“这些我看见了,但是看不见哨兵。”
“说不定他在背阴处,”老头儿解释说。“那儿现在挺热。他一定在我们看不见的背阴那头。”
“有可能。下一个哨所在哪里?”
“在桥下面。在养路工的小房边,就在山口五公里的里程碑那里。”
“这里有多少士兵?”他指着锯木厂。
“也许四个外加一个班长。”
“下面呢?”
“要多些。我会探出来的。”
“那么桥上呢?”
“一直都是两个。每头一个。”
“我们需要些人手,”他说。“你能找来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能找来多少,”老头儿说。“现在这一带山里就有不少人。”
“有多少?”
“一百多个。不过他们都分散成小分队了。你需要多少人?”
“等我们勘察完那座桥以后再告诉你。”
“你想现在就去勘察吗?”
“不。现在我想找个地方把这些炸药藏起来,到用的时候再去拿。我希望把它藏在最安全的地方,而且离桥不能超过半个小时的路程。”
“那简单,”老头儿说。“从我们要去的地方到那桥一路全都是下坡。不过,我们现在要去那儿倒是还得费力地爬一会儿啊。你饿吗?”
“饿,”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过会儿再吃吧。你怎么称呼?我忘了。”他竟把名字都忘了,这对他来说不是好兆头。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是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我帮你拿那个背包吧。”
这年轻人是个瘦高个儿,金色的头发闪着光泽,一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脸,他穿着一件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的裤子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一条胳膊伸进背包的一根皮带里,把那沉甸甸的背包甩到肩头上。然后另一条胳膊伸进另一条皮带圈里把背包正好,使背包的重量压在他的背上。他衬衫上原先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还没干。
“我背好了,”他说。“我们怎么走?”
“我们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俩被背包压得弯着腰,汗流浃背地在山坡上的松树林里一步步向上爬。在树林里年轻人根本就找不见路,但是他们继续向上攀爬,绕到了山前面,此时他们跨过了一条小溪,那老头儿稳稳地踩着溪边石块向前走去。这时,山路更加陡峭,爬山也更加艰难了,后来,那溪水竟好像从他们头顶上的一个平滑的花岗石峭壁上直泻下来一样,老头儿在峭壁脚下站住等着那年轻人赶上来。
“你能行吗?”
“行,”年轻人说。他大汗淋漓,因为爬了刚才那一段陡峭的山路,大腿的肌肉都有些痉挛了。
“在这里等我。我先去通知他们。你带着这东西总不希望自己被击中吧。”
“当然不希望,”年轻人说。“还远吗?”
“很近。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 ,”年轻人回答。他把背包卸下来,轻轻地放在溪边两块大圆石中间。
“那么就在这儿等着吧,罗伯托,我会回来接你的。”
“好的,”年轻人说。“不过你打算顺着这条路走到桥那去吗?”
“不。我们去桥那边时得走另一条路。那条路近一些,也比较好走些。”
“我不想把这东西藏得离桥太远。”
“你瞧着办吧。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另找地方。”
“我们瞧着办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边,看着老头儿攀登峭壁。那峭壁并不那么难爬,而且这年轻人发现那老头儿攀爬时两手不用摸索就能利落地找到攀手的地方,从这可以看出他之前已经爬过这地方好多次了。然而,在上面的人却小心翼翼地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他饿极了,并且心中焦虑。挨饿是他常有的事,但焦虑却不常有,因为他对自己的处境一向毫不在意,而且凭借经验他知道在这乡村一带开展敌后活动是多么容易。如果有个好向导的话,在敌后活动和在敌人防线中间穿梭一样,都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如果被敌人抓住怎么办,那事情可就麻烦了;还有就是判断信任谁的问题。你要么完全信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要么完全不信任,在这个信任问题上你必须作出决定。他发愁并不是这些。而是别的一些事情。
这个安塞尔莫是个好向导,他走山路很有本事。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是走山路的好手,不过,从黎明前跟着他一直走到现在,他知道这老家伙走起来能把他累死。到目前为止罗伯特?乔丹对这个安塞尔莫除了判断力之外,全部都信得过。他还没机会考察这老头儿的判断力,不过,不管怎样,判断都是他自己该负责的事。不,他愁的不是安塞尔莫,而炸桥也并见不得比别的许多事情更难办。不管什么样的桥,只要你叫得出名的,他都知道怎么炸,他炸过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他这两只背包里装着足够多的炸药和装备,哪怕是安塞尔莫所报告两倍大的桥,也足够把它彻底炸掉。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在徒步旅行去拉格朗哈时曾经走过这座桥,戈尔茨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的房子楼上给他念过这座桥的资料。
“炸桥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戈尔茨当时说,用铅笔指着一张大地图,灯光照在他那有伤痕累累的光头上。“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
“根本没什么大不了。仅仅把桥炸掉只能算是失败。”
“是的,将军同志。”
“要做到根据发起进攻的时机,在指定的时刻把桥炸掉。你自然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你的命令和任务。”
戈尔茨看看铅笔,然后用它轻轻地敲击牙齿。
罗伯特?乔丹什么也没说。
“你明白,这就是你的命令和任务,”戈尔茨接着说,看着他冲他点头。他用铅笔敲敲地图说:“那就是我的任务。那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茨气愤地说。“你打过那么多场战斗,怎么还问我为什么?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改变?什么能保证此次进攻不被取消?什么能保证此次进攻不被推迟?什么能保证实际进攻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在六个小时之内?有过一次战斗是按时进行的吗?”
“如果是你来指挥进攻就会准时,”罗伯特?乔丹说。
“那些从来也不是由我指挥的,”戈尔茨说。“我只是制定而已。但从来不是我指挥的。炮队不是我的。我必须提出申请。我申请时即使他们有也从来没照我的要求给我。那都还是最小的事情。还有别的事情呢。你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子。不用赘述。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有人会干预。所以现在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那什么时候炸桥?”罗伯特?乔丹问。
“进攻开始以后。进攻一开始就炸,绝不能提前炸。这样,就没有增援部队能从那条路上开上来了。”他用铅笔指着。“我必须确保那条路上不来援兵。”
“什么时候进攻?”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你只能把日期和时间当做一种可能性的参考。你必须时刻准备着那一时刻的到来。进攻开始后马上就要炸桥。明白吗?”他用铅笔指着。“那条是他们增援部队的必经之路。他们只能从那条路把坦克、大炮、甚至还有卡车运到我要发动进攻的山口。我必须确保那桥一定被炸掉。不能提前,否则如果进攻推迟的话,桥就能被修好。那绝不行。进攻一开始,它就必须被炸掉,我必须确保它被炸掉。只有两个哨岗。跟你一块儿去的人刚从那里来。据说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你到时候就明白了。他在山里有人。你要多少人就要多少。人尽量要少,但要够用。我不必跟你啰嗦这些事情。”
“怎样才能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
“进攻将由整整一师兵力发动。先有飞机轰炸开道。你耳朵不聋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飞机投射炸弹时,进攻就算开始了呢?”
“你不能总是那样想,”戈尔茨说,不住地摇头。“不过这一次,你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我设定的进攻。”
“我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我实在不太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太喜欢。你要是不愿干,最好现在就说出来。你要是觉得自己干不了,现在也说出来。”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去,没问题。”
“我只要明确这一点。”戈尔茨说。“那就是桥上绝对不能有任何东西通过。这一点务必要保证。”
“我明白。”
“我不愿意命令别人做这种事情,而且还是这种方式,”戈尔茨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去干这事。我明白因为我提出的要求,你将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我这样仔细地解释,是为了要你清楚,要你清楚可能遇到的重重困难和任务的重要性。”
“如果桥炸了,你们如何向拉格朗哈推进?”
“等到我们攻占山口之后,就会重新把桥修起来。这是一次非常复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像以往一样复杂而漂亮。这个计划是在马德里制定的。是维森特?罗霍,那位失意的教授的又一个杰作。我布置进攻计划历来都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也不例外。尽管如此,这次军事行动仍然有很大胜算。我对此次进攻行动比以往更感觉乐观。把桥炸掉,这一仗就能大胜了。我们就能拿下塞哥维亚了。你看,我指给你看战局是怎么进展的。你看到了吗?山口的顶端可不是我们这次攻击的目标。我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不止这些。看-这里-像这个-”
“我宁可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
“好,”戈尔茨说。“那样的话你就能少一点思想负担,是吗?”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那样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泄露情况。”
“那的确还是不知道的好,”戈尔茨用铅笔敲敲前额。“好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那桥的一些情况,是不是?”
“是。那我知道。”
“我相信你知道了,”戈尔茨说。“我不会再对你啰嗦了。我们来喝一杯吧。话了这么多,我都渴了,霍丹同志。你的姓氏用西班牙语念起来很有意思,霍丹同志。”
“你用西班牙语怎么念‘戈尔茨’,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茨露齿笑了笑,从喉咙深处发出这个声音,好像患了重感冒咳痰似的。“‘霍茨’,”他嘶哑地说。“‘霍茨将军同志’。如果我早知道‘戈尔茨’在西班牙语里是这样的话,我到这里作战前真该给自己取个好听一点儿的名字。我以为来指挥一个师,随便取什么名字都没关系,可是谁知道竟然取了‘霍茨’这么个名字。‘霍茨将军’,现在要改已经来不及了,你喜欢党后游击队工作吗?”这是俄语里一个表示敌后游击的词语。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露齿而笑。“在户外工作很健康。”
“我在你这个年级时也非常喜欢。”戈尔茨说。“他们告诉我你炸桥很在行。非常专业。不过这还只是道听途说。我还从来没见过你亲自做过什么。也许那都不是真的。你真的炸掉那些桥了吗?”他逗他说道。
“有时候。”
“炸这座桥,你最好不要说‘有时候’啊。别了,咱们还是别再说这桥了。你现在对这座桥已经相当了解了。我们非常严肃,所以才开得起大玩笑。那,你在战线另一边有很多姑娘吗?”
“没有,我没时间花在姑娘身上。”
"我不同意。任务越不规律,生活也就越不规律。你的任务非常不规律。再有,你得理发了。”
“我的头发理得很合适,”罗伯特?乔丹说。要他像戈尔茨那样把头发剃光还不如死了算了。“我该思考的事情已经够多啦,没时间想姑娘的事,”他沉着脸说。
“我该穿什么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不用穿制服,”戈尔茨说。“你的头发理得很不错。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跟我很不一样,”戈尔茨说着有斟满了两人的酒杯。
“你从来不是只惦记着姑娘。我根本不思考。为什么要思考呢?我是将军。我从来不思考。别想引诱我去思考吧。”
有个师部的人员坐在椅子上,正在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这时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对戈尔茨大声地说了些什么。
“闭嘴,”戈尔茨用英语说。“我想开玩笑就开。正因为我很认真,才能开玩笑。现在把酒喝了就走吧。你明白了吗,嗯?”
“是,”罗伯特?乔丹说。“明白了。”
他俩握了手,他敬了礼,出来上了师部的汽车,老头儿等在里面,已经睡着了。他们乘这辆车一路经过瓜达拉马镇,老头儿还在睡觉,再顺着上纳瓦塞拉达的公路,开到登山俱乐部的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儿睡了三小时之后才出发。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茨的情景,戈尔茨的脸白得出奇,永远也晒不黑,鹰一样的眼睛,大鼻子,薄嘴唇,剃光的头上有着一条条皱纹和伤疤。明天晚上,部队将集合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黑漆漆的公路上,长长两行车在夜色中装载着步兵;配备沉重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把他们的枪支抬上卡车;坦克顺着垫木开上装坦克的长平板车;在深夜把一师兵力拉出去,调动布置,准备进攻山口。他不愿想这些事。那不是他的事。那是戈尔茨的事。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而且必须把它计划得清清楚楚,把所有的情况都估计到,不能发愁。发愁和恐惧一样糟糕。这只会使事情更难办。
这是,他坐在小溪边,望着山石间清澈的水流。他发现溪水对面有一簇稠密的水田芥。他涉过小溪,拔了两把,在水流中把根上的泥洗净,然后返身坐在背包旁,吃着那干净而凉爽的绿叶和鲜嫩带辣味的茎梗。他跪在溪边,把系在腰带上的自动手枪挪到背后,免得弄潮。他两手各撑在一块岩石上,附身去和溪水。溪水冷彻骨髓。
他撑起身体,转过头来,看见老头儿正在悬崖上爬下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这地区几乎成为制服的农民黑罩衣和深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还背着一支卡宾枪。这人光着脑袋。两人像山羊般灵活地从悬崖上爬上来。
他们向他走来,罗伯特?乔丹站起身。
”你好,同志,“他对背卡宾枪的人说,并且微微一笑。
”你好,“对方勉强地说。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个人满是胡子茬的大脸。这张脸盘差不多是滚圆的,脑袋也是圆圆的,紧挨在肩膀上。两只眼睛小而分得很开,一双耳朵小而紧贴在脑袋上。他身子粗壮,高五英尺十英寸左右,大手大脚,鼻子破裂过,嘴角一边被刀砍过,横过上唇和小颌的刀疤在丛生的胡子中露了出来。
老头儿对这个人点点头,微微一笑。
”他是这里的头儿,“他露齿笑着说,然后屈起双臂,仿佛要使肌肉鼓起来似的。他以一种半带嘲弄的钦佩神情望着这个背卡宾枪的人。”一条好汉。“
“我看得出来,”罗伯特?乔丹说,又笑了笑。他不喜欢这个人的神情,心里没有一丁点儿笑意。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份?”背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把别住衣带盖的安全别针解开,从法兰绒衬衫的左胸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交给这个人,这个人摊开证件,怀疑地看看,在手里翻弄着。
罗伯特?乔丹看出他原来不识字。
“看这公章,”他说。
老头儿指指印鉴,背卡宾枪的人端详着,把证件夹在手指间翻来翻去。
“这是啥公章?”
“你以前从没见过?”
“没有。”
“有两个,”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S.I.M.-军事情报部。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
“对,那个公章我以前见过。不过在这里要我说了才算数,”对方阴郁地说。“你包里藏的什么?”
“炸药,”老头儿神气地说。“昨晚我们摸黑越过了火线,今天一整天,背着这炸药走山路。”
“我用得着炸药,”背卡宾枪的人说。他把证件还给罗伯特?乔丹,上下打量着他。“对。炸药对我很有用。你给我带来了多少?”
“我带来的炸药不是给你的,”罗伯特?乔丹平静地对他说。“炸药另有用处。你叫什么名字?”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他叫巴勃罗,”老头儿说。背卡宾枪的人阴郁地望着他们俩。
“好。我听到过很多夸你的话,”罗伯特?乔丹说。
“你听到关于我的什么话?”巴勃罗问。
“我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游击队长,你忠于共和国,并用行动证实了你的忠诚,你这个人既严肃又勇敢。我给你带来了总参谋部的问候。”
“你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注意到这个人一点也不吃马屁。
“从布伊特拉戈到埃斯科里亚尔,我都听说,”他说,提到了火线另一边的整个地区。
“布伊特拉戈也好,埃斯科里亚尔也好,我都没熟人,”巴勃罗对他说。
“山脉的另一边有很多人从前都不是住在哪里的 。你是哪里人?”
“阿维拉省人。你打算用炸药干什么?”
“炸毁一座桥。”
“什么桥?”
“那是我的事。”
“如果它在这片儿,那就是我的事。你不能在紧挨你住的地方炸桥。你必须住在一个地方活动在另一个地方。我的事我了解。一个在这活了一年多的人,知道他自己的事。”
“这是我的事情,”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可以一起商量。你愿意帮我们拿那两个包吗?”
“不。”巴勃罗摇着头说。
老头儿突然转过身,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勉强能听懂的方言,快速而愤怒地对巴勃罗说话。仿佛是在朗诵克维多的诗篇。安塞尔莫说的是古卡斯蒂利亚语,大意是:“你是野兽吗?是呀。你是畜生吗?一点不错。你有头脑吗?不,没有。我们现在是要来干一件重要极了的大事,可是你倒好,只想着自己的安乐窝不被惊动,把你自己的狐狸洞摆在比人类的利益还重要的位置上。看得比你同胞的利益还重要。我去你的八辈祖宗。赶紧把包背起来。”
巴勃罗把头低了下去。
“人人都得根据实际情况干他力所能及的事,”他说。“我住在这里,就到塞哥维亚以外的地方活动。你要是在这一带山里搞乱子,我们就会被从这里赶出去的。只有按兵不动,我们才能在这一带山里待得下去。这就是狐狸的原则。”
“是啊,”安塞尔莫尖刻地说。“这是狐狸的原则,可我们偏偏需要的是狼。”
“我比你更像狼,”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知道他一定会拿那个背包的。
“嘿,嗬……”安塞尔莫冲着他说,“你比我更像狼,我都六十八啦。”
他往地上啐了一口,摇了摇头。
“你有这么大岁数吗?”罗伯特?乔丹问,看到暂时没事了,就尽量让气氛缓和些。
“到七月份就整六十八岁喽。”
“我们要是能活到那月份就好了,”巴勃罗说。“我来帮你背这个包,”他对罗伯特?乔丹说。“另一个让老头子背。”他现在的口气不是愠怒,而差不多是伤心的。“这老头子力气可大着呢。”
“这个包我来背,”罗伯特?乔丹说。
“不用,”老头儿说。“让另一个大力士背。”
“我来背,”巴勃罗对他说,在他的郁怒的神情中包含着一丝悲伤,这使罗伯特?乔丹感到忐忑不安。他理解这种悲伤,可在这里看到还是令他担心。
“把卡宾枪给我背吧,”他说。巴勃罗递给了他,他把枪扛到背上。那两人走在前面带路,他们手脚并用地攀登那个花岗石峭壁,艰难地翻过山脊后,就来到了树林里的一片绿色空地上。
他们沿着这块空地的边缘走着,此刻的罗伯特?乔丹肩上卸下了沉甸甸的、使人出汗的背包,换上了硬邦邦的卡宾枪,轻快愉快地迈开了大步。他四处留神观察,发现这里有几处草皮被牲口啃掉了,地上还有系马桩的痕迹。他看见出草地上有些马的新鲜粪便,还有一条牵马到小河边去饮水时踩出来的小径。他想:他们晚上把马匹拴在这里吃草,白天再把马儿们藏到树林里,不知道这个巴勃罗究竟有多少匹马。
此时他回想起了当时无意间注意到巴勃罗裤子的膝盖和大腿部分被磨得油光锃亮。他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马靴,是不是穿着那种麻绳鞋骑马。他一定有全套装备。他想着:我可不喜欢他那股愁苦劲儿。那不是什么好事。人们在放弃或者背叛前才表现出那种愁苦。那是出卖别人之前表露出来的愁苦。
在他们前面,有一匹马在树林里嘶叫,只有些许阳光从那浓密得遮天蔽日的树顶中透下来,顺着那些松树的褐色的粗树干的缝隙,他看到了用绳子绕着些松树树干围成的马圈。他们走近时,马儿们都把脑袋转向他们,马鞍都堆放在马圈外的一棵树下,用柏油帆布遮着。
他们走到近前时,背包的两人站住了脚,罗伯特?乔丹知道他该把这些马恭维一番了。
“太好了,”他说,“这些马真漂亮啊。”他转向巴勃罗。“你可有一支骑兵小分队呢。”
那里面共有五匹马:三匹枣红色马,一匹栗色马和一匹鹿皮色马。罗伯特?乔丹把它们先都大略地扫了一眼,然后再逐匹打量,仔细鉴别。巴勃罗和安塞尔莫清楚这些马有多棒,此时的巴勃罗骄傲地站着,脸上的愁苦少了几分,温情地注视着这几匹马,老头儿的样子仿佛表示这些马是他自己突然间变出来的似的。
“你看这些马怎么样?”他问。
“都是我的好马呀,”巴勃罗骄傲地说,罗伯特?乔丹很高兴听到他这样说话。
“那,”罗伯特?乔丹指着一匹一只白色前蹄兼前额带白斑的枣红色公马,“是匹好马。”
那匹马美得仿佛是从委拉斯凯兹 的画作里走出来的一样。
“它们都是好马,”巴勃罗说。“你懂马吗?”
“懂。”
“那还不赖,”巴勃罗说。“你看得出其中一匹有点儿小毛病吗?”
罗伯特?乔丹知道这个不识字的人正在考验他呢。
这些马儿仍都抬着脑袋望着这个人。罗伯特?乔丹从马圈围栏的两道绳索中间钻到里面,拍拍鹿皮色马的屁股。他向后靠在围栏的绳索上看着那些马在马圈里面兜圈子,又站直了打量了它们一会儿,等它们停下来时,他弯腰从绳子中间钻了出来。
“栗色马靠外侧的一条后腿有点瘸,”他冲巴勃罗说,眼睛并不看着他。“那蹄子劈了,如果好好钉个马掌的话,不会马上出大问题,不过如果在硬地上走得多的话,就会废掉。”
“我们弄到它的时候,那蹄子就是这样,”巴勃罗说。
“你最好的马,那匹白额枣红色公马的炮骨上有个肿块儿,我可不喜欢。”
“那不要紧的,”巴勃罗说。“那是三天前撞的。要是有问题的话,早就有问题了。”
他掀开柏油帆布,亮出马鞍。有两幅普通的牧马人的马鞍,类似美国西部牛仔使的马鞍;一副十分华丽的牧人马鞍,手工打造的皮面上有精美的雕花,还配着一副厚实的带脚盖的马镫;另外还有两幅军用的黑色皮革马鞍。
”我们杀了两个民防兵,“他解释那两个军用马鞍的来历。
”那可是个大战利品啊。“
”他们在从塞哥维亚到圣玛利亚德尔雷亚尔的那段路上下马的。他们下马来检查一个赶车人的证件。我们在那杀了他们,没有伤到马匹。“
”你们杀了很多民防兵吗?“罗伯特?乔丹问。
”不多,“巴勃罗说。”不过杀了人没伤到马匹的就只有这两个。“
”是巴勃罗在阿雷瓦洛炸的火车,“安塞尔莫说。”那就是巴勃罗干的。“
”有个外国人和我们 一起干的,是他炸的,“巴勃罗说。”你认识他吗?“
”他叫什么?“
”不记得了。名字很古怪。“
”他长什么样子?“
”金色的头发,和你一样,不过没有你高,一双大手,鼻梁是断的。“
”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可能是卡希金。“
”没错,“巴勃罗说。”就是类似这么个古怪的名字。他怎么样了?“
”他四月份就死了。“
”谁都难免一死,“巴勃罗沮丧地说。”那是我们大家的结果。“
”那是所有人的结果,“安塞尔莫说。”人固有一死。你怎么回事,伙计?你肚子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他们很厉害,“巴勃罗沮丧地看着那些马,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道。”你们还不知道他们有多厉害。我眼看着他们越来越强大,武装也越来越好。物资越来越丰富。可我这里只有这几匹马而已。我能指望什么呢?要么被追捕要么战死。再没别的啦。“
”人家追你,你也在追人家呀。“安塞尔莫说。
”不,“巴勃罗说。”再也会了。一旦我们现在离开这片山区,我们能到哪儿去?你能告诉我吗?现在能到哪儿去?“
”西班牙有的是山地。离开了这里,还可以去格雷多斯山 啊。“
”我才不去那呢,“巴勃罗说。”我厌倦了被人追来追去的。我们在这里待得好好的。现在如果你在这里把桥炸了,那我们又要被人追捕了。一旦他们知道了我们在这里,就会用飞机来搜索我们,他们一定就会发现我们的。如果他们派摩尔人来扫荡,他们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就得走。我讨厌这一切。你听见了吗?“他转向罗伯特?乔丹。”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权利跑到我这来对我指手画脚,支使我必须干什么?“
”我没有支使你非得干什么,“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你会的,“巴勃罗说。”那。那就是祸根。“
他指着他们刚才看马时卸下来放在地上的那两个沉甸甸的背包。看到那些马似乎勾起了他满腹的烦恼,而看到罗伯特?乔丹懂马,似乎又让他吐露了心事。他们三人站在围绳边,斑驳的阳光洒落在那匹枣红色色公马的身上。巴勃罗看看它,然后用脚磕了两下那沉甸甸的背包。”这就是祸根。“
”我来只是为了执行任务,“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是奉指挥官的命令来的。如果我向你请求帮助,你可以拒绝,我可以找其他愿意帮我的人。我甚至还没开口请你帮忙呢。我必须遵守命令,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任务的重要性。我是外国人,可这不是我的错。我倒宁愿生在这里。“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这里不要惹上麻烦,“巴勃罗说。”对我来说,我现在的责任是保护我的手下和我自己。“
“你自己。是啊,”安塞尔莫说。“你早就对自己负责了。对你自己和你的马。没有马的时候你和我们一条心。现在有了马你也变成一个资本家了。”
“这句话不公平,”巴勃罗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一直贡献我的马的。”
“少得可怜,”安塞尔莫轻蔑地说。“我看少得可怜。要是用来偷东西,可以。为了吃得好点,可以。为了杀人,可以。为了打仗,不行。”
“你这个老头儿,早晚坏在你这张臭嘴上。”
“我这个老头儿谁都不怕,”安塞尔莫对他说。“还有我这个老头儿没有马。”
“你这个老头儿是活腻歪了。”
“我这个老头会长命百岁,”安塞尔莫说。“而且我可不怕狐狸。”
巴勃罗什么也没说却拿起了背包。
“还不怕狼,”安塞尔莫说着拿起了另一个背包。“如果你是狼的话。”
“闭上你的嘴,”巴勃罗对他说。“你这个老头儿真是罗里啰嗦。”
“我这个老头儿言出必行。”安塞尔莫被背包压弯了腰。“还有他现在饿啦。也渴了。快赶路吧,哭丧个脸的游击队长。带我们去找点吃的。”
罗伯特?乔丹心想,开头就真够不顺当的。不过安塞尔莫是条汉子。他想,他们好的时候真了不起啊。他们好的时候,谁都比不过他们,而他们坏的时候,谁也都不如他们那么恶毒。安塞尔莫把我们带到这来一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是我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
好在巴勃罗在背背包而且还把卡宾枪给了他。罗伯特?乔丹觉得,也许他一直就是这副模样。也许他只是天生阴郁的人。
不对,他对自己说,不要自欺欺人啦。你不知道他过去什么样;可是你知道他现在正迅速地变坏而且毫不掩饰。而一旦他开始掩饰的时候,就已经打定了主意。一定要记住,他告诉自己。一旦他作出第一个友好的表示,那他一定已经打定主意了。不过这些马可真不错,他想,真是漂亮的马啊。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有那种巴勃罗对那些马的感情。那老头儿说得对。那些马让他发了财,他发了财就想享受。他心里想,我猜他马上就会感觉不好了,因为他不能参加赛马会。可怜的巴勃罗。轮不到他参加赛马会。
这想法让他感觉好了一点儿。他笑着看前面两个人驼着背背着大背包在树林里穿行。他一整天都没和自己开玩笑,不过现在他开了一个,自己感觉好受多了的。你变得越来越像他们这些人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你也变得沮丧了。他当然对戈尔茨感到沮丧无奈。这个任务让他有点难以招架。有那么点难以招架,他想。非常难以招架。戈尔茨是快活的,而他想让他离开前也快活快活一下,不过他没有。
所有杰出的人,只要你稍微细想一下,就知道他们都是快活的。快活是好得多,而且快活还意味着别的。好比你还活着就已经得到了永生。这个很难说得清。不过他们所剩无几。那些快活的人没剩几个了。只剩下可怜的几个了。如果你继续想这些的话,嘿,伙计,你也剩不下了。现在别想了,老家伙,老同志。你现在是一个要炸桥的人。不是一个思想者。我饿了,他想。我希望巴勃罗是个讲究吃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