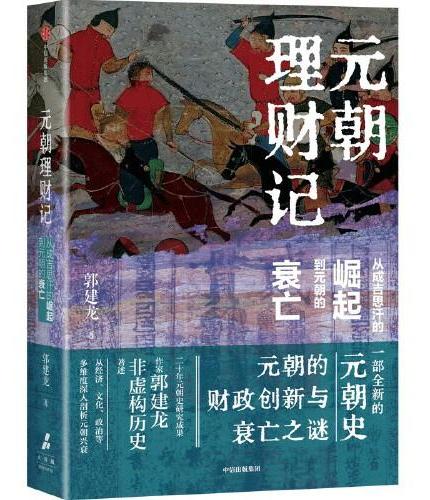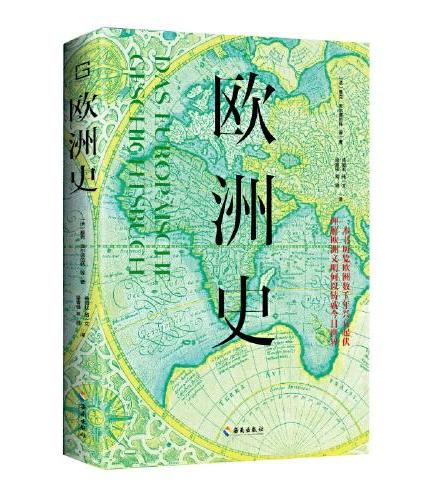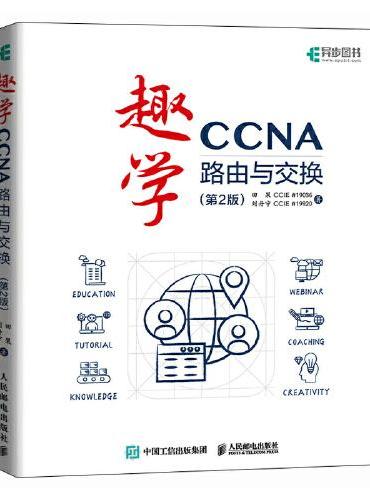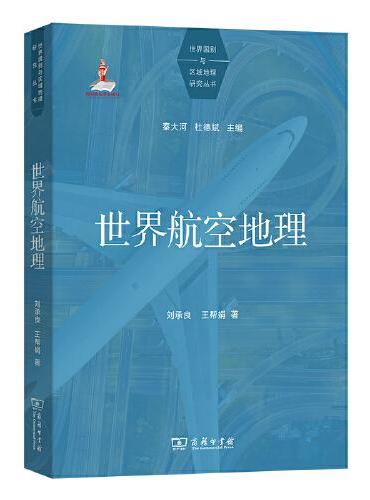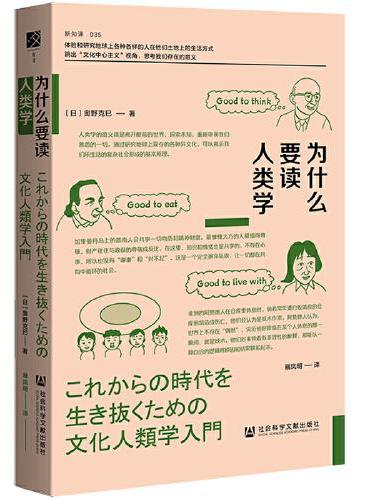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
》
售價:HK$
98.6

《
我真正想要什么?:智慧瑜伽答问/正念系列
》
售價:HK$
5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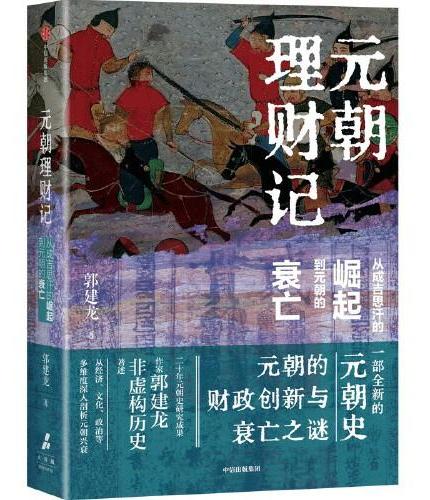
《
元朝理财记 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
》
售價:HK$
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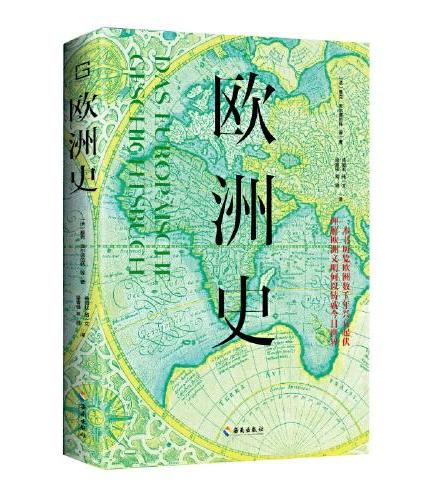
《
欧洲史:一本书历览欧洲数千年兴衰起伏,理解欧洲文明何以铸就今日世界
》
售價:HK$
3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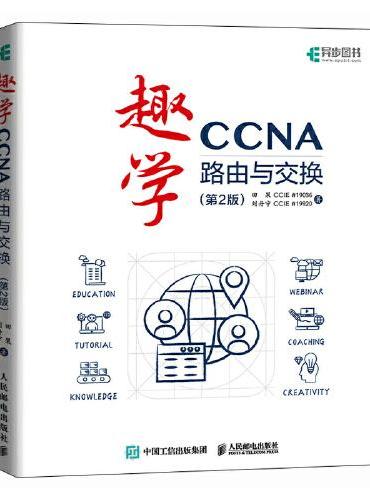
《
趣学CCNA——路由与交换(第2版)
》
售價:HK$
1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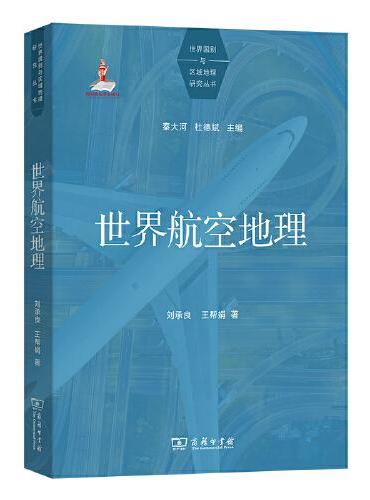
《
世界航空地理(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研究丛书)
》
售價:HK$
244.2

《
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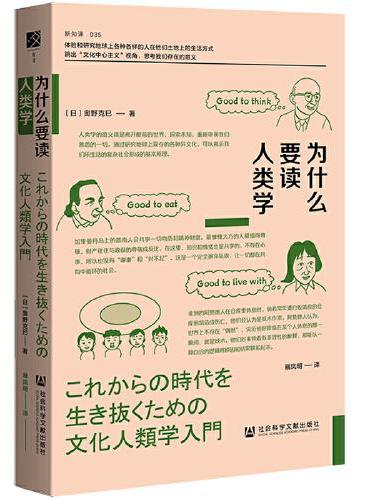
《
为什么要读人类学
》
售價:HK$
77.3
|
| 編輯推薦: |
杨照先生本来以冷静、犀利、透彻的评论文章见长,但当他转向“青春”这个永恒话题,再次来到那个“长久失去、仿佛拾回、却又无从确知的君父城邦”,像大多数人一样,依然无法抑制自己久违的、幸福的战栗。
青春总是在寻觅出口,总是在遗憾,总是在迷路。
|
| 內容簡介: |
《迷路的诗》以忏情开始,回忆作者在高中时代的浪漫与叛逆。三十多年前,当杨照面对初萌的青涩恋情,少年时代的苦闷与彷徨、迷惘与骚动,诗成了最重要的出口;对文学与知识的热情也透过诗歌传递。
相隔十五年,此次新版重新问世,杨照除了新添短序一篇外,更把当年没说尽的话,新增成《诗和少年时光》长文收入书中。并将校园生活的情怀以照片记录在书里。老师同学更翻箱倒柜,挖出杨照当年编的《建中青年》校刊,历历往事也再次鲜活地搬演了起來。
著名作家张大春也因与作者杨照交往数十年,特别撰文分享他对这位曾经迷路的诗人的特殊认识。
|
| 關於作者: |
杨照,本名李明骏,1963
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曾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 总监、台北艺术大学兼任讲师、《新新闻》周报总编辑等职;现为《新新闻》周报总主笔、博理基金会副执行长,并为News98
电台“一点照新闻”、BRAVOFM91.3 电台“阅读音乐”节目主持人。
长篇小说──《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大爱》《暗巷迷夜》。中短篇小说集──《星星的末裔》《黯魂》《独白》《红颜》《往事追忆录》《背过身的瞬间》。
散文集──《军旅札记》《悲欢球场》《场边杨照》《迷路的诗》《Cafe
Monday》《新世纪散文家:杨照精选集》《为了诗》《故事效应》。
文学文化评论集──《流离观点》《文学的原像》、《文学、社会与历史想象》《梦与灰烬》《那些人那些故事》《Taiwan
Dreamer》《知识分子的炫丽黄昏》《问题年代》《十年后的台湾》《我的二十一世纪》《在阅读的密林中》《理性的人》《雾与画:战后台湾文学史散论》。
现代经典细读系列──《还原演化论:重读达尔文物种起源》《颓废、压抑与升华:解析梦的解析》《永远的少年:村上春树与「海边的卡夫卡」》。
近作──《故事照亮未来》《我想遇见你的人生》。
微博:weibo.comyangzhao63
|
| 目錄:
|
诗人迷路了吗? 张大春
新版自序
迷路的诗
谜与禁忌
另一种真理的探求
潮一般的感伤
在有限的温暖里
夜 雨
气 味
浪漫之阙如
遗落月亮
如雪的声音
仿佛在君父的城邦
记忆与遗忘
一九八○备忘录
Dear You…
绣有莲花的一方手帕
旧日情怀与现实思索
迷路的诗Ⅱ
诗和少年时光
|
| 內容試閱:
|
那年,我疯狂地写了一大批以“Dear
You”开头,这样的书信。从十六岁写到十七岁半。这些信大部分用HB的硬心铅笔,刻着细如蝇头的字体,写在八开大的白报纸上。白报纸是从校刊社里干来的,本来的“正常用途”应该要拿去印公假单,印好密密麻麻的格子之后,每个想请公假的人一早就把自己的姓名班级座号填好,一张足可以替全社编辑请整天公假都还有余。我们显然是严重地高估了公假单需要的消耗量,申请来的白报纸剩了一迭又一迭在庶务柜里。我就动用当社长兼主编的特权挪来作计算纸,及写信。
字和纸张简直不成比例,可能需要四五千字才填得满一张纸。所以写完一封信,底下就又接上另一个开头“Dear
You”及另一封信。有的纸上密密麻麻写了二十几个“Dear You”。
这些信现在都还躺在旧家的抽屉里,像一堆曾经嚣张炫耀过,而今却安份守己耐心等待挖掘的考古遗物,记忆与生命故事的遗迹。
这些信当然从来没有寄出去过。因为没有地址好寄,那个收信人只活在我心里,不,她死在我心里。
真的不了解年少时候的自己,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悲怆与愁凉。彷佛只有在凄哀的悲剧气氛里,才能找到真正的美丽。这是专属那个时代的早熟深沉?还是少年浪漫的普遍特质?我真的不了解。
我只知道那时节的自己,幻想认识一个女孩子,一位最单纯最甜丽最善体人意的少女。然而认识时她已经罹患绝症。只能陪着日益衰病的她走过短短的路程,终点到了我们就下车。不,她就下车了,我留在生命的车上继续听着总也不肯停熄的引擎轰隆轰隆、轰隆轰隆。
想象中她长眠在观音山。因为观音山是我唯一知道有墓园的地方。我从淡水坐渡船远眺观音山。我一次又一次独自去爬观音山。有一段石级是我最熟悉的,拾级而上时,我默默地幻想她的一生,尽可能填补从小到大所有遭遇的每一分细节。石级到顶后,离墓园大约还有十分钟的斜坡路。我一定停在石级尽头,不会再往上走任何一步。细细的汗珠急急地从每一颗毛孔里爬出来,凉凉的风则急着在它们汇流前将它们收干。
那风格外的干而且凉,像是沾过石灰粉的手掌,令人难忘。吹了一阵风,我再循原路走下山,沿路看远方的淡水河和台北市小小的火柴盒房子。
我给了她一个名字。可是无论如何频密激动地呼唤,邢名字都不像真的。不像风吹来的感觉那么真实。比风还要空洞的名字愈叫愈令人心虚与心慌。所以下笔写的时候就只剩下“Dear
You”,这样一个单瘦而且不符合英文使用惯例的书信开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