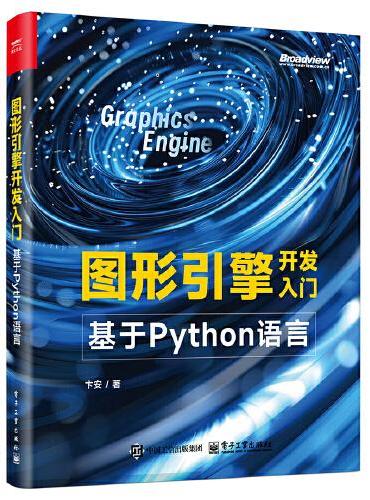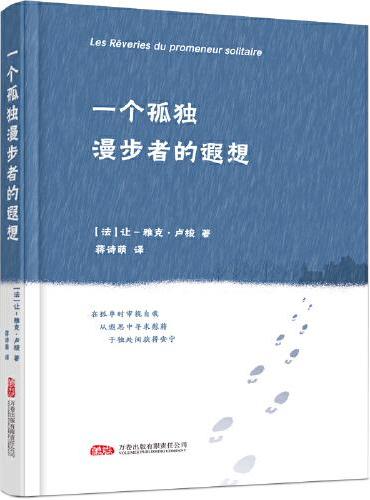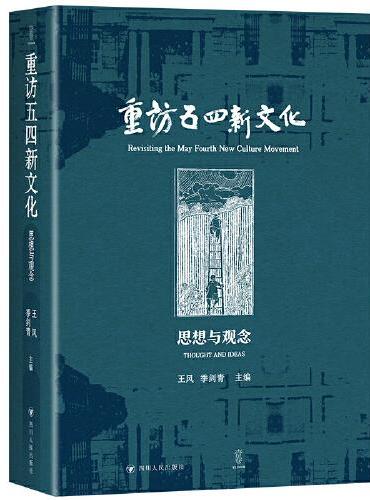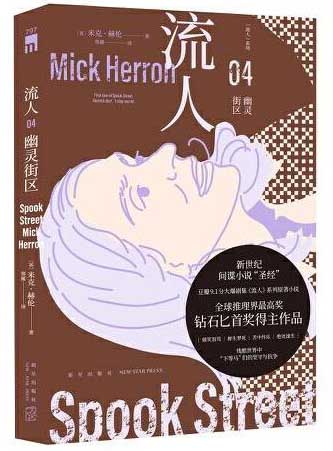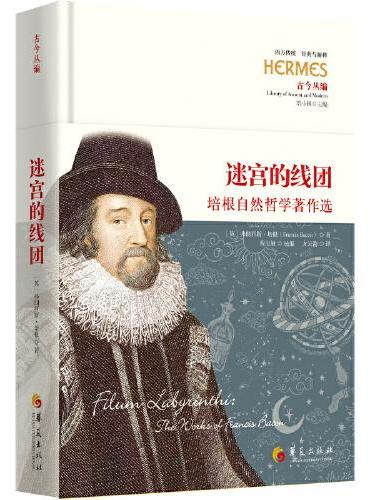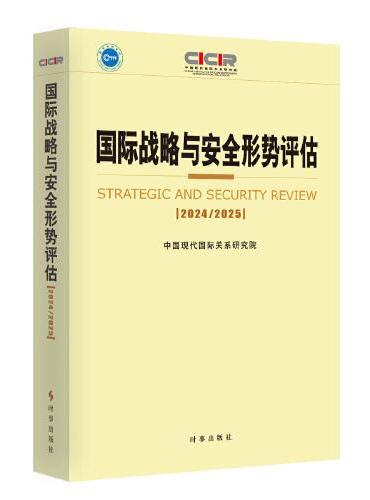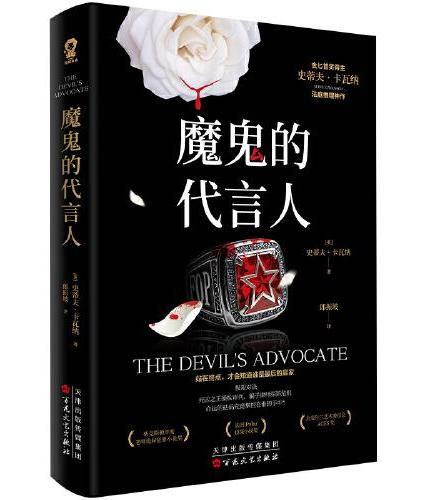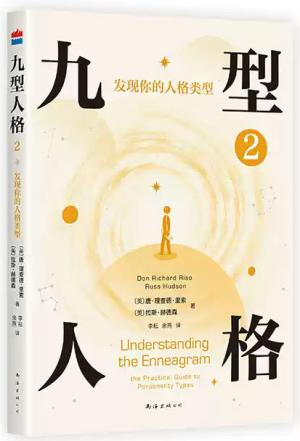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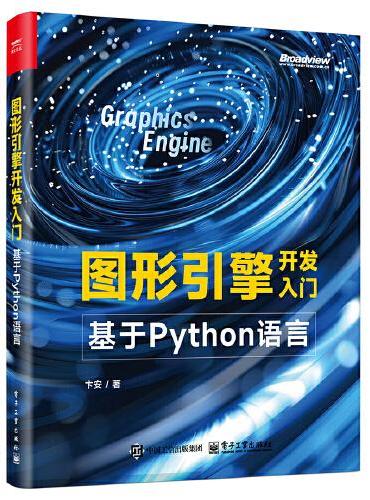
《
图形引擎开发入门:基于Python语言
》
售價:HK$
1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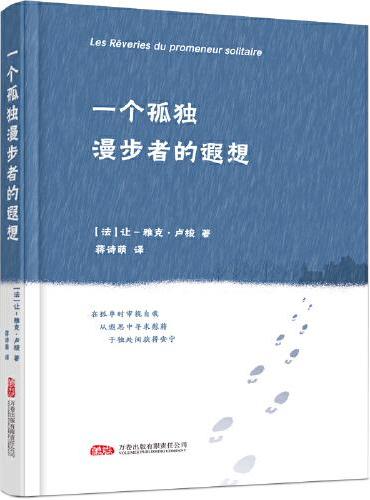
《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
售價:HK$
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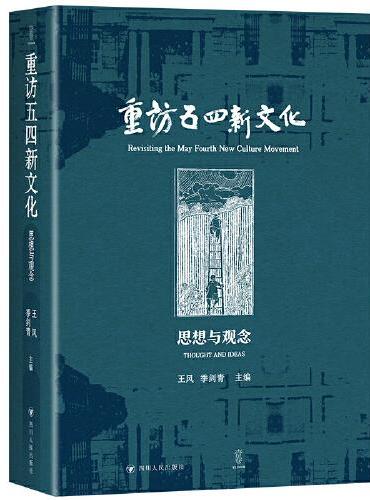
《
重访五四新文化:思想与观念(跟随杰出学者的脚步,走进五四思想的丰富世界)
》
售價:HK$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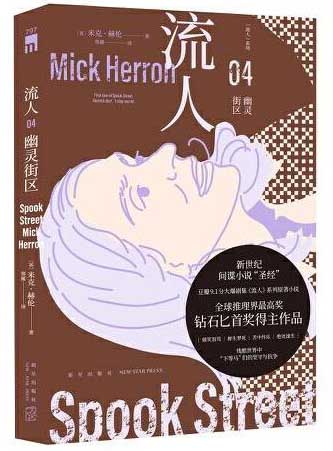
《
流人系列04:幽灵街区 午夜文库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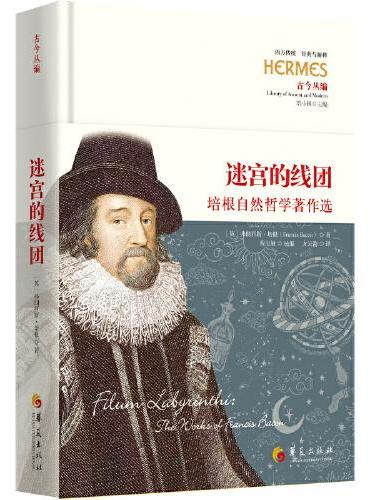
《
迷宫的线团:培根自然哲学著作选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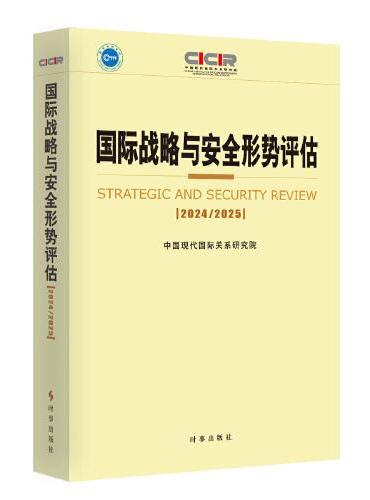
《
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4-2025
》
售價:HK$
1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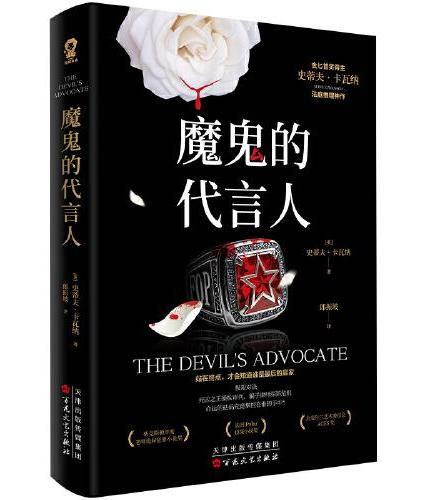
《
魔鬼的代言人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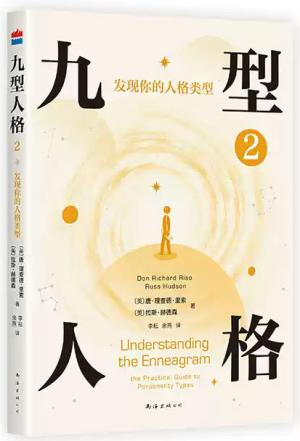
《
九型人格2:发现你的人格类型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
《孙中山演讲录》辑录孙中山讲稿30余篇,分为“思想”、“革命”、“军事”、“党务”、“政务”、“观念”、“实业”、“外交”等8个部分,还原了历史现场感和时事感,折射出一代伟人为建立现代化民主国家之理想,进行的各种思考、探索、尝试,也能看到他代表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形势所做的判断。对今天的思想者、为政者,仍大有启发。
|
| 內容簡介: |
|
《孙中山演讲录》分为“思想”、“革命”、“军事”、“党务”、“政务”、“观念”、“实业”、“外交”等8个部分,总共收录演讲稿35篇,共计370千字。演讲具有场合性、时事性。这些演讲稿,语言平实,思路清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伟人为建立现代化民主国家的理想所进行的各种思考、探索、尝试,也能看到他代表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形势所做的判断,包括今日的中美日关系,今后世界发展的方向等等。《孙中山演讲录》有利于增加普通读者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建国方略的了解,对学者乃至为政者,相信也有很好的助益。
|
| 關於作者: |
|
孙中山(1866.11.12—1925.03.12),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
| 目錄:
|
第一篇 答记者问
与伦敦各报记者的谈话(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致伦敦各报主笔函(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与伦敦记者的谈话(一八九六年十月下旬)
附:与林奇谈话的报道(一九○一年春)
与刘成禺的谈话(一九一○年二三月间)
我的回忆——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
与英国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
与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间)
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间)
与上海《民立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间)
与上海《大陆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与驻沪外国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下旬)
在南京答《大陆报》记者问(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
致《字林西报》等书面谈话(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接见麦考密克时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一至二月间)
在南京答《字林西报》记者问(一九一二年三月六日)
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
在上海答《民立报》记者问(一九一三年八月一日)
在广州与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在广州与报界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
在广州答香港电报公司代表问(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与香港《士蔑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五月上旬
在广州对报界公会主任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三日)
在香港与《士蔑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日)
在上海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在上海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上海与《大陆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香港与《南清早报》记者威路臣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六月)
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七月中下旬)
在塘沽与某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北京与《大陆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与《亚细亚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在北京与各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
在北京答记者黄远庸问(一九一二年九月四日)
在北京与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与《中国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在北京招待报界同人时的演说和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在济南记者招待会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对《大陆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十月五日)
在日本下关答记者问(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三日)
在日本与新闻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三年二月中旬)
在香港对《早士蔑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在上海对某记者的谈话(一九一六年六月八日)
在上海与徐朗西的谈话(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五日)
答广州某报记者问(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与广州各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在广州与某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在日本门司对记者的谈话(一九一八年六月十日)
自门司赴箱根途中与泽村幸夫的谈话(一九一八年六月十日)
在上海答记者问(一九一八年八至九月间)
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与《益世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与上海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年十一月八日)
与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与《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与日本东方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二日)
与《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七日)
与东方通讯社特派员的谈话(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与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的谈话(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二日)
与美国记者辛默的谈话(一九二一年四月上旬)
在广州与苏俄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一年四月)
与美国记者金斯莱的谈话(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与美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上、中旬)
与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四月中旬)
与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与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六月上旬)
与广州报界公会及各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与香港《士蔑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与香港《电闻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与香港《士蔑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旬)
与报界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与客人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驻沪特派员村田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与约翰·白莱斯福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
与《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一月八日)
与国际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与国闻通信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与东方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与广州各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
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
与某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三年十月初)
与某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与东方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与胡特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
与北京《东方时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与克拉克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与国闻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八日)
与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与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与《东方通信》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
与香港某电报通社访员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与日本广州新闻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三月)
与日本广东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九月上旬)
与东方通信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与日本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与东方通信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与东方社等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与日文《广东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在上海与欢迎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与《申报》记者康通一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与日本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与驻沪外国新闻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与高木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间)
与大阪《英字新闻》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与《告知报》记者代表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JP4〗关于民主政治与人民知识程度关系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与日本记者西村等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与日本某访员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第二篇 与客人谈
与邓廷铿的谈话(一八九六年十月十四日)
在伦敦苏格兰场的陈述词(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向英国律师卡夫所作的陈述词(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四日)
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一八九七年初)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一八九七年八月中下旬)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一八九七年八月至一八九八年八月间)
离横滨前的谈话(一九○○年六月上旬)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一九○○年七月十日)
与宫崎寅藏的谈话(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一九○○年八月中旬至二十一日间)
与章太炎的谈话(一)(一九○二年春)
与章太炎的谈话(二)(一九○二年春)
与刘成禺的谈话(一九○二年)
与旅比中国留学生的谈话(一九○五年二月)
与陈天华等的谈话(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与汪精卫的谈话(一九○五年秋)
与胡汉民的谈话(一九○六年四月中下旬)
与芙蓉华侨的谈话(一九○六年七月十七日)
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与章太炎的谈话(一九○六年十二月)
与池亨吉的谈话(一九○七年一月五日)
与东京同盟会员的谈话(一九○七年一月)
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一九一○年二月中旬)
与梅乔林等的谈话(一九一一年五月五日)
与鹤冈永太郎的谈话(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间)
与胡汉民的谈话(一九一一年以前)
与冯自由的谈话(一九一一年以前)
与张永福的谈话(一九一一年以前)
在广州行辕与各界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六月九日)
与送行者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与招待员施愚等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与汤漪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在北京与陆徵祥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与袁世凯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与某人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在北京与袁世凯的谈话(一九一二年八月)
在北京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二日)
与某人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三日)
与袁世凯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上旬)
与梁士诒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上旬)
在北京回访四国银行团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上旬)
与广东旅京同乡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在北京广济庙与旗人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在北京迎宾馆与某君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上中旬)
在日本与陪同人员的谈话(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四日)
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的谈话(一九一三年四月九日)
在东京与某某的谈话(一九一六年四月)
游西湖时的谈话(一九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游览杭州时的谈话(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七、十八日)
关于不任铁道协会会长的谈话(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与旅沪党人总事务所代表的谈话(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与苏赣督军代表的谈话(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接见国会议员代表的谈话(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在上海与李宗黄的谈话(一九一八年七月)
与邵元冲的谈话(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与谢□焦□的谈话(一九一九年五月)
与戴季陶的谈话(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与邹鲁的谈话(一九一九年六月)
与邵元冲的谈话(一九一九年夏)
与童杭时的谈话(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中旬)
与邵元冲的谈话(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与马立成等的谈话(一九二○年一月十四日)
与蒋梦麟的谈话(一九二一年九月上旬)
与梁鸿楷等的谈话(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与海军将士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与陈炯明调和代表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在永丰舰上的谈话(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
与夏税务司的谈话(一九二二年七月十日)
在摩轩号舰对幕僚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
在“俄国皇后号”邮船上的谈话(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与郭泰祺的谈话(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与郦朴的谈话(一九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与吴南如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与王用宾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与学生代表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三月七日)
与王宠惠杨天骥的谈话(一九二三年四月下旬)
与张开儒等的谈话(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
与杨文炤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与叶恭绰等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与旅粤桂省人士的谈话(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与广东籍某议员的谈话(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
与梁士锋何振的谈话(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在广州与各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与美使舒尔曼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一月六日)
关于时局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
与日人某君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二月)
与大本营法制委员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关于台山县自治办法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与菲律宾劳动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与英国驻广州领事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
与广州各社团代表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在北伐第五次军事会议的谈话(一九二四年九月四日)
与党员同志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与蒋中正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与某君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与何世桢等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与青年党员某君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与石克士等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在长崎与欢迎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门司与来访者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与张作霖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
在天津答拒毒会某教士问(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与某君的谈话(一九二五年)
与叶恭绰许世英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与马伯援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与许世英的谈话(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与葛廉夫的谈话(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与宋庆龄的谈话(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与汪精卫等的谈话(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与汪精卫的谈话(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与何香凝的谈话(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对汪精卫等的口谕(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临终前的谈话(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
| 內容試閱:
|
附:与林奇谈话的报道 一九○一年春
孙逸仙乐意地谈及他最近组织的革命活动“。他取下地图,指出作战地点和起义者的进军路线。说明他们失败的原因,仅是由于缺乏弹药,他们指望从一个日本承包商那里取得弹药,但那人欺骗了他们。
孙逸仙说:“对于斗争的结局,我们毫不气馁,事实上恰好相反。因为起义表明,我们的人一旦获得适当的武装并且作好大举的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军。”接着,他谈及起义的详情。战斗仅仅持续了二十天。他从不到六百人开始,这些人只有三百支来福枪,每支枪三十发子弹。十天之内,他们从清军手中夺取了一千支来福枪。到二十天结束时,他们的人数也由六百增加到二万。第一场战斗发生在沙湾附近,这里紧靠英国新领土香港对面的边界。边界由英国人管辖,由于英国人偏袒清军,在这里逮捕了不少起义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朝东北方向挺进,并在沙湾与三多祝之间进行了十二场战斗,所有这些战斗都打了胜仗。在最后一仗中,他们的弹药完全耗尽。打完了最后的弹药,显然已无法守住阵地,他们便悄悄解散回家。孙说:“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愿意解散,要是我能及时赶到那里,他们没有弹药也将坚持战斗。可是当时我正在邻国忙于准备工作,他们就只好解散了。”起义者一共只牺牲了五个人,而清军有五百人被击毙,一百人被俘。起义者占领了两个重镇和许多村庄,他们严禁任何劫掠和纵火行为,人民很快转而拥护他们。
……在听了孙关于这个小战役经过的叙述以后,我问他是否认为,除进行一次革命外,中国便没有实现改革的希望?他回答说:
“凡是了解中国朝廷,了解包围和影响皇帝的那些人物的,谁都应当知道,清朝皇帝没有能力去有效地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激烈改革。”孙逸仙及其朋友们的抱负,是发动一次有如三十年前日本所发生的革命,希望在中国实现日本化。他满怀信心地认真谈论这一题目。我问及中国人民是否会像日本人那样,准备实行改革,他答道:如果中国人民得到合适的领袖人物的率领和指导,他们是一定愿意的;大多数人民都会依照他们所得到的指示去做。于是他就以热烈的态度,简直是热情洋溢地谈到了他的同胞的优越性——他们的高超智慧、他们的模仿力以及学习新事物和汲取新思潮的能力,都超过日本人。他说:“日本人用了三十年才办到的事情,我们最多用十五年就能办到。”他并且提出很多技艺和工业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论点。……他久久地畅谈他的目标和计划。他拥有一批优秀的、被他称为新式中国青年的追随者,他们曾在英国、火奴鲁鲁和日本等地受教育,其中一些人家道殷实,必要时能为革命提供需要的资金,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拯救祖国的唯一方法。
孙逸仙说:“我们开始下一次努力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当一次起义或暴动扩展成革命规模之时。”他希望西方国家将保持中立,不要加以干涉。
我评论说:“这确是一个伟大的抱负。”
他喷出一大口雪茄烟,开始在房里踱步,徐缓地说:“是的,这是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然后他继续谈及中国,谈到它的辽阔土地、众多人口和尚未开发的资源,谈到一旦发生像日本有过的那样一场伟大觉醒时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我暗示,实现他的抱负将会酿成真正的“黄祸”,他回答说,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战的民族。他说:“我们已达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你们正在开始以召开海牙会议来努力达到的。
产生黄祸的唯一可能会是在工业竞争的形式之中;俚在变动了的情况下,生活舒适的程度和工资的比率将会很快上升,因此,无需再把中国劳工廉价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去。”他以日本近三十年来工资和物价的迅速增长作为例证。他笑着说:“你对新式的中国人有些什么想法?我料想你没有见过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尽管他们在美国和日本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他们都被共同的希望和抱负所鼓舞。”
我很少碰见过比孙逸仙更有趣的人物了。……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政统治,这是孙逸仙的愿望。而且,正如他所说的,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亵渎了神明,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蹂躏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
据王冀寄赠的原文影印件《展望》第67卷第12期纽约1901 年3月23日英文版林奇《两个西化的东方人》Two
Westernized Orientals译出陈斯骏译,金应熙、黄彦校P8-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