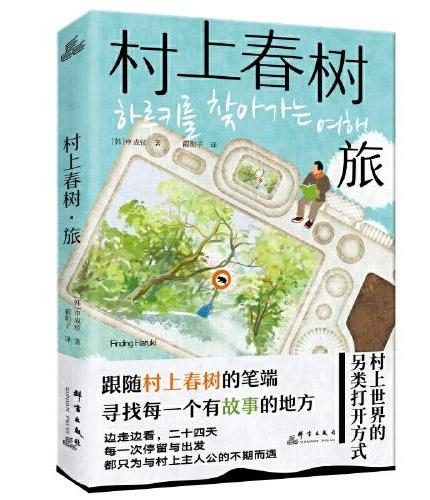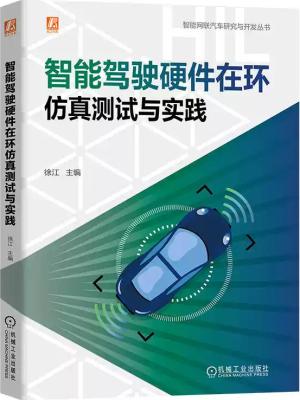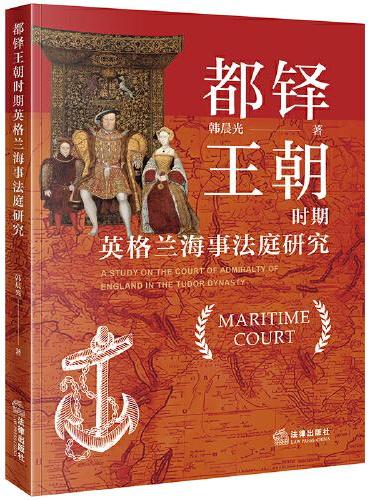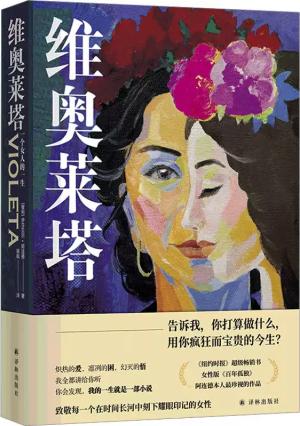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从工具到实例
》
售價:HK$
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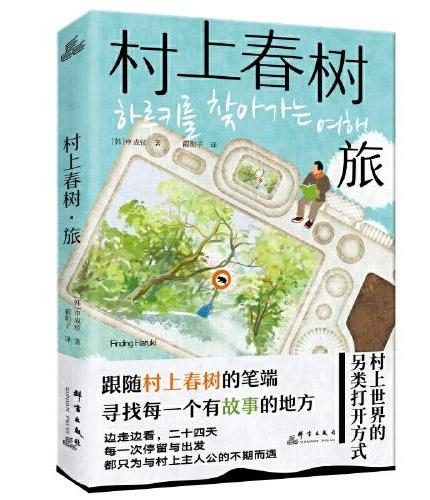
《
村上春树·旅(一本充满村上元素的旅行指南,带你寻访电影《挪威的森林》拍摄地,全彩印刷;200余幅摄影作品)
》
售價:HK$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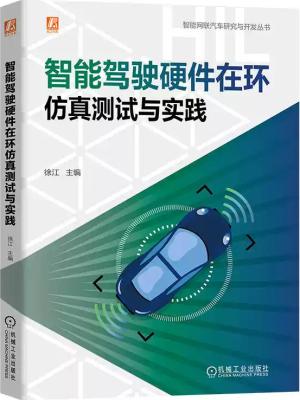
《
智能驾驶硬件在环仿真测试与实践
》
售價:HK$
1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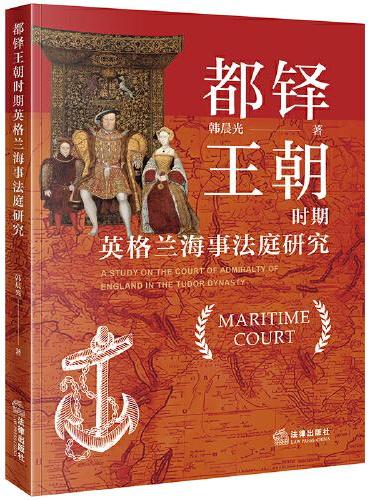
《
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海事法庭研究
》
售價:HK$
87.4

《
中年成长:突破人生瓶颈的心理自助方案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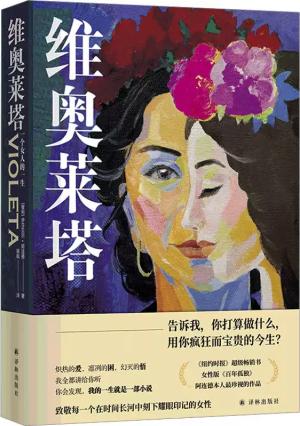
《
维奥莱塔:一个女人的一生
》
售價:HK$
76.2

《
商业银行担保管理实务全指引
》
售價:HK$
144.5

《
信风万里: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全二册)
》
售價:HK$
178.1
|
| 內容簡介: |
民国时期是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整个中国历史中少有的乱世;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动荡、大辉煌的时代,是科学与民主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的历史转折关头。从文明进步意义上说,它已超越了任何一个朝代的乱世与所谓的“盛世”。在这样一个纷乱中暗含着文明与进步的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产生了一批特立独行的大师级人物,而这批人物的家庭背景、气质、爱好、学行、处世方式等等诸方面各不相同,中西交汇,文化碰撞,数十位文化大师在短暂的民国时代巨星云集,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丽奇观,从而构成了20纪上半页中国历史星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在这个风景的正面和背面,映照出的是清华研究院五位大师的身影;是霸气横生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傅斯年那冲天的怒吼;是“三百年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那孤独的回望;是一代佳人林徽因与冰心的恩怨是非;是吴宓与毛彦文的“柏拉图之恋”,是一代狂人刘文典力踢蒋介石的奇闻轶事,是著名学者闻一多在死神面前从容镇静的面容……
本书讲述了民国大师们的飞扬与落寞,崇高与卑微……还原了他们极具人性的隐秘历史。文中融入了作者深重的生命体验,其叙述生动,史料丰富,见解独特,在此类作品中风格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喜爱。
|
| 關於作者: |
|
岳南,东诸城人,1962年生,先后毕业于诸城五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著有《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天赐王国》《风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另著有以自由知识分子学术精神与情感命运为主体脉络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李庄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南渡北归》(三部曲)等十余部,其中《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遭遇兵圣》《千古学案》《万世法门》(合著)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为中国最具全球影响的当代著名作家之一。
|
| 目錄:
|
一、清华国学院共有几位导师
二、马衡缘何未能进入史语所
三、1937:北大、清华的最后一课
四、胡适的书生大使生涯
五、孔祥熙与齐鲁大学的一段隐秘
六、胡福林因何不辞而别
七、傅斯年说:我是三等人才
八、傅斯年为何大骂郭沫若
九、李敖为何狂咬大师李济
十、林徽因与冰心结怨的背后隐密
十一、傅斯年为何轻视冰心
十二、林徽因室内飞机残片的真伪
十三、陈寅恪被困香港的原因
十四、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十五、傅斯年拒绝支付陈寅恪薪金
十六、陈寅恪投奔燕大始末
十七、金岳霖、朱自清留恋的名媛
十八、钱昌照与沈怡、胡适的恩怨
十九、臧克家比陈梦家差在何处
二十、陈梦家之死
二十一、刘文典怒踢蒋介石
二十二、闻一多与刘文典的怨仇
二十三、蒋介石没有下令刺杀闻一多
二十四、周作人称傅斯年是“驴鸣”
二十五、刘文典、潘光旦落选院士的隐秘
|
| 內容試閱:
|
一、清华国学院共有几位导师
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解体已近八十年,岁月的风尘湮没了许多令人怀念的往事,师生们的身影也在朦胧的荷塘月色中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但留在校园和学术界坚实的足迹仍清晰可辩,历久弥新。大师们所显现的人格光辉,与点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圣火,像一盏永不息灭的指路明灯,引导后学继续向着前方的路走下去。
按通常流行的说法,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四大”没错,但以为整个国学院的导师共四位那就错了。清华国学院终其一生,称为导师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陈、赵“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1911年2月,清政府在北京城内设立的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西北郊外的清华园办公,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这年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自此,中国教育史又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
最初的十几年中,清华学堂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相对薄弱。1924年初,随着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清华学堂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1]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一一聘请。很快,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相继被聘为教授。——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年轻的陈寅恪放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得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骏马中的“赤兔”,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出神入化之奇境。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曾不无感概地说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Cambridge区之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卖淫之生活实况,又欧美男女迟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说至为详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2]纵观吴宓一生的为人为学与人格品行,此话当是处于真心仰慕之情而发之。
至于这“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的称号最先由谁呼起,后来的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3]张仲述即当年与赵元任、胡适等人一同赴美留学的张彭春,属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胞弟,时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赵元任到清华做教授,主要是张的举荐,而陈寅恪则得意于吴宓与王、梁二位导师的荐举。
杨步伟所说,是李济进清华之前的事,当李氏入主国学院之后就成为五位导师了。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4岁入书房从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据李济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说:“他那表叔,是一个老秀才,最喜欢打闷棍,所以他(李济)现在虽说记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处,却记得那头上发了几次块垒。”
[4]这些故事是当年李济在台湾大学教书时告诉张的,张听后觉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认是一种事实存在。1907年,李济随时为小京官的父亲进入北京两个著名中学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关于这一人生转折,用李济后来的话说“等到清华招考的时候(也就是宣统二年),虽说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进洋学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们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个,并且我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进清华还是在前清的时候。进了清华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虽说政治上起了变动,清华并未停课,秋天我仍然进了学校。”[5]到了1918年,即一个叫列宁的世界级政治人物领导俄国工人“一声炮响”夺取政权之后,突然受到一个叫卡普兰的女特务刺杀,差点丢了性命的那一年(见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的那一年。李济结束了八年的清华学习生活,以官费生的身份,悄然无声地去了西方属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开始“放洋”生涯。与他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和自费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总干事叶企孙;著名学者董时、张道宏、查良钊、刘叔和,还有一个同船赴美筹备造反事宜的职业革命家汪兆铭。当然,坊间名气最大者除当年曾叫喊“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后来当了中国头号汉奸的国贼汪兆铭(精卫),应算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著名诗人徐志摩。这年的9月14日,船抵美国旧金山,李济与诸友分手,与徐志摩等几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就读。李与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关系极为密切。李主攻心理学,徐攻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0年暑期后转赴伦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并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哈佛创建以来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E.A.Hooton)、罗兰oBo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并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最突出的现象”。
[6]当这一研究课题基本完成后,李济把博士论文中的主要内容综合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英语短文,刊载于1922年2月美国巴尔的库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刊,以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同年12月,美国人类学会在波士顿举行年会,与会者均为当时美国顶尖的人类学家。李济在导师和鼓励下,将本年2月发表的论文稍加修订,参加年会并公开宣读。令李济和他的导师颇感欣慰的是,入会者听完报告,对这位年轻的东方学子独特见解和不凡的学识报以热烈的掌声。未久,这份报告便在1923年123期《哈佛研究生》杂志刊出,这篇“中国民族之科学研究第一部著作”,(吴相湘语)引起了学术界更加广泛的注意。此时,大哲学家罗素(1920年曾到中国讲学)正在修订他的著作《中国问题》,在读了李济的论文后,“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随即征引了一些段落补入了他的著作中。由于罗素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和大师地位,随着著作的问世,被他引用了论文的李济也跟着名声大噪。
1923年,李济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之形成:一个人类学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7]完成。此著根据111个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质,从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发展,十大姓氏的起源与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况,综合出中国民族的五种重要成分,堪称对中国民族的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所应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共同效仿的标杆而经久不衰。也就是这部著作的问民,使年仅27岁的李济荣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者。
荣得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与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的途程。一只鲜活亮丽的“海龟”就这样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曾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城。此时的“海龟”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龟”有着较大不同,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个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大亨的追求。从徐志摩于哥伦比亚大学致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被徐称作“刚毅木纳,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8]“老兄”,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所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活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9]回国后的李济,在一位叫凌冰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时期结识的学长举荐下(南按:当时凌担任南开大学部主任,一说教务长),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丁氏作为曾在欧洲剑桥、葛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归国的老字号”海龟“,此时已取得了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地位,甚为学界同仁推崇敬仰。
年轻又具有远大抱负的李济,自从和这位”风采翩翩,学问渊博,见解超人,“而且”性格爽朗,直率,做事颇有决断“的”丁大哥“做了一番交谈后,从”非常投机“,很快转化为”更加佩服。同时还发现,丁文江先生有许多意见,实在与我自己的意见有很多相符合的地方。“”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10]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正是这种志同道合的血性与因缘,使二人结成终生挚友。这时的丁文江正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而正在这个时候,河南新郑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传到北平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丁文江得知这一消息,便鼓动李济亲自前往现场做些发掘工作,并筹了二百块大洋作为发掘经费,同时还派地质调查所谭锡畴作为助手,目的是”寻找该地区内是否有任何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李济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郑作了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由于土匪捣乱与河南人不肯合作,加上墓葬几乎被盗墓贼盗掘一空,发掘收获不尽人意,李济自觉有”失败“之感,但还是从具体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可贵的田野工作经验,并有简短的英文报告《新郑的骨》问世。[11]按李济的说法”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
正是因了这番苦心,使年轻的李济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或许,正如许多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飞船弦梯,迈向月球加里加特死海之时发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声音:“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李济在新郑发掘的第一步,也正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迈出的一大步,具有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大幕将在这轻轻的脚步声中正式拉开,神秘的东方古代文明之门将轰然洞开,使整个地球人类为之震撼。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佛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所作的最早贡献,毕士博由北京的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李济当时认为自己“虽说是在美国作过五年学生,但与外国人没共过事。”因而当收到信时,颇为踌躇,最后“就决定请教''丁大哥''去。”丁文江认真听完李济的陈述后,直截了当地说:“教书固然是很好,研究更为重要。”因而主张李选择研究工作,并且列举了几件很显赫的事例,以证明他如此看的理由。同时丁告诉李,与外国人相处,重要的是“直道而行”,且“开始就把条件讲清楚。”[12]听了丁文江的“箴言”,李济决定与对方合作,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行提出了合作的两个决定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接信后即回华盛顿,向他的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顺便将李济赞扬一番,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13]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于是便辞去南开的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从而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李济语)打下了基础。
就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也鸣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光辉前景,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曹一听李济的经历和名声,立即决定聘请。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
助理员:周光午。
[14]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人称赞,向以木纳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声称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15]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歪理邪说而被无情地抛之于九霄云外了。
从清华国学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人数,特别是有名望的“海龟”尚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认同,在此发挥了交叠的作用。就整个导师队伍论,此时的李济虽有大师的身价,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士林却没有把他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并列而成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前“四大”的教授头衔,其实内中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与详情,而这些详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模糊淡远,遂成为后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段历史公案。
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说法,一种是,由于李济当时正和美国费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
[16]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
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荐李济时,曹一开始欲聘李为研究院专职教授,与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个“五大导师”,即当年西蜀霸主刘备手下“五虎上将”的阵营,以威天下。当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奉命与李济接洽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曹校长所想的那样简单,对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特别倾心的李济,因此前与毕士博已经签约,不太愿意完全放弃在费利尔艺术馆考古队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劳的机会,是否到清华做全职教授犹豫不抉,他向吴宓提出的公开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此两难情形由吴宓禀报曹云祥,经过曹、梁、吴、丁等人共同商谈,认为李济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中国第一位攻读人类学的“海龟”,其学术前景不可限量,决定采取让李济一担挑的方式两头兼顾,聘为特别讲师。丁文江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李劝说,认为清华研究院的工作性质与南开毕竟不同,在南开是纯粹的教书,而在清华则以研究为主,所带学生不过几人而已,谓李“不要放弃作第一手科学研究的机会”云云。[17]李济听了丁的劝导,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华周刊》第345期“新闻”栏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来校,与吴宓博士晤谈。闻校中拟请其任教授,惟恐有碍Bishop(毕博士)先生方面之考古事业,则李先生暂任讲师云云”。另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如下记述:“下午二时,李济如约来,愿就聘。以特别讲师为宜。”[18]据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这一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来清华讲课,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是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据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称,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函询其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结果毕士博继续聘李济与之一同进行考古发掘,李济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讲师。”
[19]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李光谟在分析了几乎与孙敦恒所述清华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说“看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终其''一生''(四年之久),也仅仅在第一批导师中有四位是教授衔的,称他们为''四大'',也的确是实至名归。”[20]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吧。
当然,那时的李济并不知道日后会为“几大”与“几位”问题,产生如此繁乱的纠葛与争论,他只是带着自己的兴趣与志向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清华园去实现他的理想。从当年清华的“官方文件”上看,李济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之后,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其间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他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期间,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另半个是徐中舒(徐为第一届研究生,主要从王国维研读古文字学与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济的名下只能算半个)。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们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当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因为梁对李有推荐保举之恩,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在清华任教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这个时候的李济正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费利尔艺术馆毕士博的支持下,即开始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使其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和更广阔的前景,于是便有了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6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教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组建考古陈列室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欲研究吾国古代之文明,人类进化之程序,典籍以外,尤必资藉于实物及遗迹之考察也。”[21]乃议决由研究院与历史系合办考古学陈列室,由两部教授合组一考古学室委员会,公推李济为主席,主持其事,每年经费预算六七千元。借此契机,这年9月,李济与北京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袁复礼同赴山西,开始了调查发掘古物的田野考古之旅,并很快在夏县发现了著名的西阴村遗址。二人组织当地民工在此发掘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
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研究院。梁启超看罢又惊又喜,连夜给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专业的儿子梁思永写信,信中颇为激动地谈到了这批出土器物,并详细叙述了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等问题,并说道:“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对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极富科学眼光的梁启超说:“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
[22]梁启超殷切期望在美读书的梁思永好好研习学问,回国后跟着李济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事业。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进行的发掘事业,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它在以坚实的出土材料否定了瑞典人安特生氏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同时,也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由这次成功发掘而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探索与实践之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并以“中国考古学之父”而载入史册。
[1]《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吴宓《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吴宓诗集?空轩诗话》,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
[3] 《四年的清华园》,赵杨步伟 , 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
[4、5、6] 《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7]《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载《传纪文学》第一卷第五期,1962年10月1日,台北出版。
[8] 《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载《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
[9、13] 《我与中国考古工作》,载《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0、12]《关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载《丁文江印象》,雷启立编, 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
[11]原文载于Transactions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Vol.3.1926.
[14、17、18、19、21]转引《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15]《王国维遗书》5,《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
[16] 《致李光谟》,戴家祥
,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戴是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据载云:当时的清华研究院有王、梁、陈、赵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间,助教一名。李济同样得到了一间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届毕业生王庸(字以中)。根据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导师谈话。
[20] 《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杨振宁等著 ,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22]《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