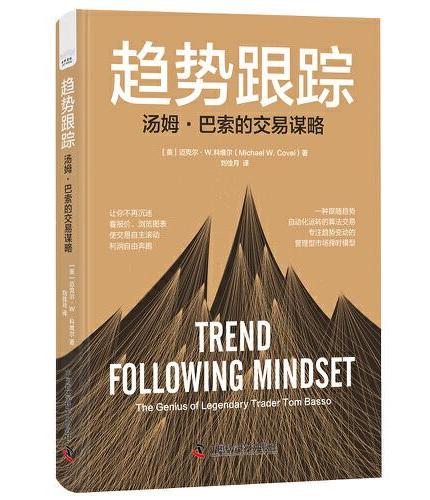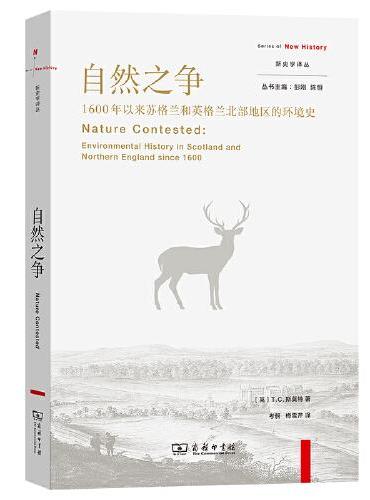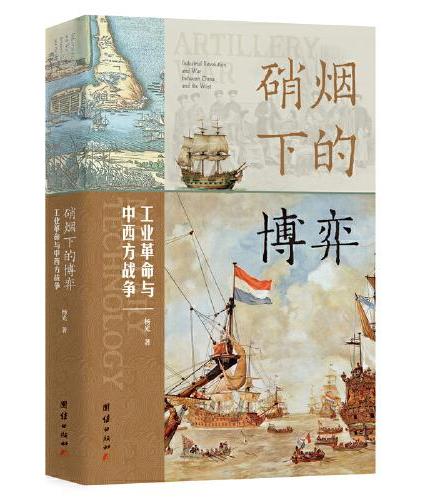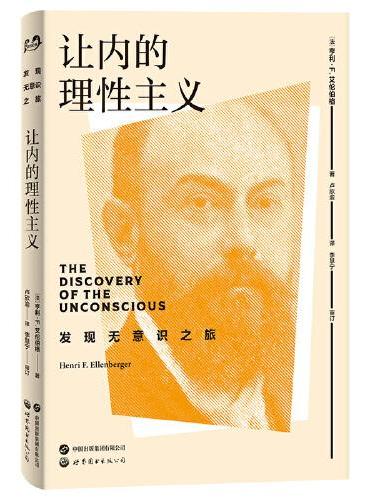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如何成为一家千亿公司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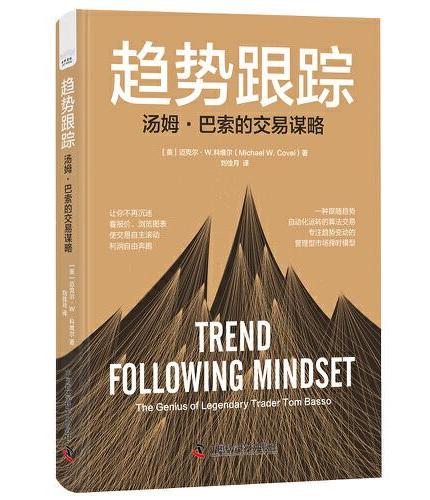
《
趋势跟踪: 汤姆·巴索的交易谋略
》
售價:HK$
77.3

《
滚滚红尘(《滚滚红尘》电影原著)
》
售價:HK$
54.9

《
罗马之变(法语直译,再现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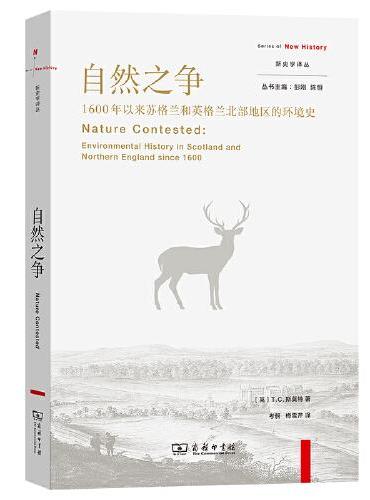
《
自然之争:1600年以来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地区的环境史(新史学译丛)
》
售價:HK$
10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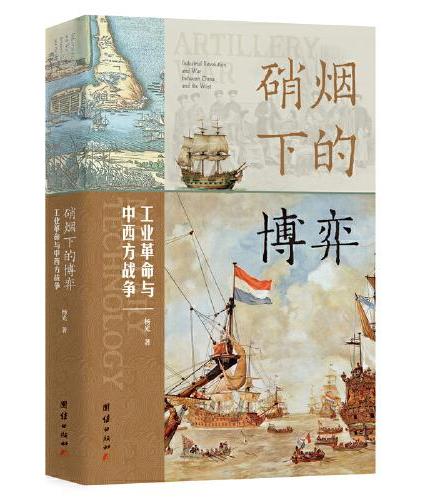
《
硝烟下的博弈:工业革命与中西方战争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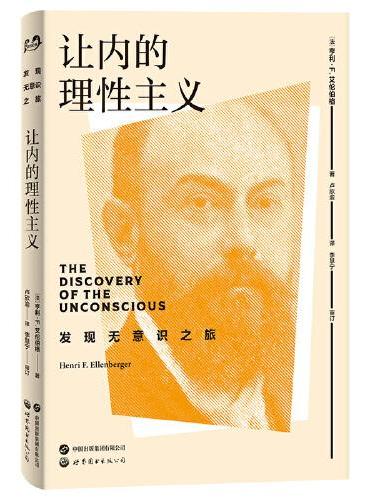
《
让内的理性主义 发现无意识之旅
》
售價:HK$
66.1

《
苏美尔文明(方尖碑)
》
售價:HK$
132.2
|
| 編輯推薦: |
|
本书是一个哈佛医学生在四年学程上的临床见习实录。在整个见习过程中,所触及的不但是患者肉体、精神的苦痛与挣扎,更直接窥探了往往令人无言以对的生命奥义。此外,书中面对高度敏感的医患关系的矛盾与纠葛有相当精彩的剖陈。
|
| 內容簡介: |
|
艾伦·罗思曼医生以生动的文笔,娓娓道出自己在哈佛医学院的四年中,如何由懵懵懂懂“白袍加身”的一年级学生,历经不同的学习阶段及兴奋、骄傲、沮丧甚至是后悔的心路历程,最终在毕业后正式成为医生时,意会到这身白袍的意义。而白袍所带来的沉重责任感,更让作者了解到,身为医者的学习成长将永远没有止息的一天。
|
| 關於作者: |
艾伦·罗思曼
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曾任职于波士顿儿童医院与波士顿市立医院小儿科住院部,目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区作医务服务。
|
| 目錄:
|
前言:崭新的白袍
哈佛第一年
走进哈佛
解剖实验室
急诊室的故事
了解性生活史
远大理想
临终关怀
哈佛第二年
触诊之虑
首次体检
疾病名称
价值观的冲突
妇科检查
事业与婚姻
表演秀
医师资格考试
恐怖的一关
外伤急救
失语症病人
我的医学之路
两年临床实习
外科实习
医疗程序
难相处的病人
无法承受之痛
妇产科实习
治疗性人工流产
难熬的病房实习
儿科的快乐时光
杰米的故事
艾滋病患儿
内科实习
昔日猛虎
绝望的挣扎
双重关系
鸟语者的选择
精神科病房
拒绝吃药的杰茜卡
询问的力量
煤矿小镇哈泽德
重返急诊室
毕业时刻
译者后记
|
| 內容試閱:
|
[序]
崭新的白袍
“你绝对猜不到今天我做了什么!”罗伊在电话那头冲我嚷道。他刚从医院回来,今天他要跟随一位医生给病人看病。
罗伊是我们班第一个给病人作直肠检查的人。实际上,除了量血压以外,这是我们所有人迈入临床的第一关。今天的门诊很特别,因为文质彬彬的罗伊不得不操作了三次前列腺检查:一次是在医生面前,还有两次是在医学院的学生面前。同样不自在的还有病人,他和罗伊都觉得很尴尬。
当我向我妈妈讲述了罗伊的遭遇之后,她觉得难以置信:病人怎么会允许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来检查他的前列腺呢。她问道:“病人真的同意了吗?”
对于病人的默许,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罗伊身上的白袍。穿上白袍几个月后,我就习惯了病人对我的信任,哪怕这种信任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的一位同学向病人提问以便得出诊断结果时,由于对患者的疾病不是很了解,所以不得不问道:“嗯,你能再详细地跟我说说这种病是怎么回事吗?”
病人回答道:“我还以为你能告诉我呐。”
新生入学培训第一天的“白衣典礼”上,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件胸前绣有“哈佛医学院”深红色草体字样的白袍。为了便于管理,整个年级被随机分成了4个小社团哈佛医学院实施小班教学,整个年级分成Peabody,Cannon,Castle及Holmes
4个小社团,每个社团约有30~40人左右,随后再分为几个小组。作者所在的社团叫做霍姆斯社团(Holmes)。——译者注。每一个社团独立举行典礼,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吃午餐。霍姆斯社团的仪式一点儿也不隆重。穿着崭新而陌生的白袍,我们都有点儿不好意思,偷偷地互相打量着。在社团办公室门口,大家乱哄哄地排着长队领白袍,我排在队伍的后面,轮到我的时候,小尺寸的都发完了,只好领了一件很大的白袍。
“你可以和别人换一下。”行政助理对我说。
一天之后,穿着还有新衣折痕的白袍,我们以医学界正式成员的身份第一次参与了门诊。
白衣典礼是学校管理层想出来的,目的是在入学的第一天,正式宣告我们迈入了医学的大门。虽然我们的白袍没有医生或住院医生的长,但这件白色制服意味着我们已经加入到医者的行列当中,不再是普通人或者志愿者了。
作为一年级学生,这种身份我受之有愧。在学习了解剖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生理学、遗传学和胚胎学之后,我深刻感受到自己并非学得太多,而是知道得太少。不过在每周一的“病人-医生”课程哈佛临床教学从一年级就开始了,课程叫“病人-医生”课程,分三个阶段。——译者注上,我还是会穿着白袍去会见病人。
尽管我在医学领域中的位置还是未知数,但这身白袍已经把我带进了一个陌生而千变万化的医患世界里。对病人来说,白袍象征着公众赋予医生的权威和信任。大多数病人并不知道白袍的不同长度代表着不同的医学等级,在他们眼中,白袍就是白袍。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的这身白袍其实表示我只是一名“医学院学生”。这种感觉就好像我戴着“红字”,而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与病人每周进行面谈是“病人-医生”课程的一部分,目的是让我们学习提问的重点、正确的言谈举止以及如何给病人适当的答复。指导老师告诉了我们怎么获取患者详细而有条理的病史。每周我都能对着不同的病人熟练地依葫芦画瓢。这种互动的目的不仅仅是查明他们的病史,更是学习。一次,结束医院里的“病人-医生”课程后,我们走在回医学院的路上,安德烈娅感慨道:“真烦!我心里总是惦记着接下来要问病人什么问题,所以根本没仔细听病人讲述病情。你说这种情况在我这儿会改变吗?”
当我和病人面谈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我的白袍。许多病人都是70多岁的老人,22岁的我在他们面前就像一个孩子。而白袍则掩盖了我的年轻稚嫩,掩盖了我的毫无经验,也掩盖了我的惴惴不安。可是,在医学世界里,白袍非但没有给我提供隐形的庇护,反而迫使我毫无心理准备地接受这种特权。
穿着白袍,我可以随意提问,而病人也会义不容辞地回答我。他们相信我倾听他们讲述的时候不会带任何歧视;相信我会明白他们的症状和痛苦;也相信我对他们充满同情。我从病人最隐私的问题中收集信息,并且询问他们生理和心理世界中最私密的问题,而他们对我却一无所知。而且,在每周的互动中,我们被赋予了权力,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每周,我都会带着几页龙飞凤舞的笔记离开某个病房,一去不复返。他们的生活和我们之间的互动全都浓缩在我的涂鸦之作上。照顾病人的事与我无关,我的义务仅限于保守病人的秘密。
在进入医学院之前,我或许会毫不犹豫地同意让一个医学院学生给我作直肠检查,因为我也会被白袍所蒙蔽。我非常感激病人们给我这种机会,让我学会了问诊和简单的检查。我渴望有朝一日能用精湛的医术回报他们,我渴望自己某一天能成为真正的医生。
两年临床实习
外科实习
她是我手术室里的第一个病人,而我不知道她是谁。在等候区第一个带窗帘的小隔间里,这位身材臃肿的黑人妇女正躺在手推床上。护士将她推入手术室之前,我看到她的丈夫和她吻别。刚进手术室,她就请我替她保管一张手写的祈祷卡片。我不知所措,一个护士为我解了围,把卡附在了她的病历里。护士们把她转移到手术台上,并用棕色的无菌碘酒清洁她的腹部,碘酒干了之后呈金黄色。她们用一块消过毒的绿色毛巾在腹部围成了一个手术区域,以免受到身体其他部位病菌的感染。麻醉师给她实施了麻醉之后,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深度睡眠之中。
手术室和我想象中一样,有白色的地板和绿色的瓷砖墙,乳白色的环形灯发出暖色的光,照着病人的腹部。当病人熟睡时,几个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各种颜色的监测数据和曲线。呼吸机随着她的呼吸起伏发出有节奏的嘶嘶声。房间的两侧是工作台,手术室门的上方挂着一个提示时间的简易钟表。
“她是转移性乳腺癌晚期,”在外科医生开始手术前,一个住院实习医生告诉我,“她现在出现了肠梗阻的症状,因为肿瘤已经转移到结肠上了。”
我看着外科医生划开了第一个切口。当手术刀沿着腹部划下去时,黑色的皮肤立刻在刀下崩开,露出淡金色的脂肪层。就像是被剥去半透明外皮的柔软橘瓣,脂肪里渗出了微量的深红色血液。外科医生用电烙器止血,当出血区域炭化成泡状的黑色时,脂肪发出的滋滋声盖过了仪器发出的嗡嗡声。医生继续用手术刀划开金黄色的脂肪层,并灼烧那些破裂的毛细血管来止血。最后,医生的手术刀把脂肪层下的大肠剥露了出来。脂肪层被剥离腹壁后,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被肿瘤侵袭的大肠。我瞥见她泡泡糖般的粉红色大肠在腹腔内静静地蠕动着,而且闪闪发亮,它们隔着橘红色的球状脂肪带在腹腔内蜿蜒迂回地紧密排列着。
我被这情景震撼了,没想到薄得令人惊讶的深棕色皮肤之下,却是淡黄色的脂肪,下面还有明亮的肠道和橙色的脂肪。以前,我们在尸体上看到的各个脏器都是单调的暗灰红色,所有器官自然地混为一体。现在这些器官鲜艳的色彩和生动的构造真是出人意料。
7月,临床实践一开始就是令人生畏的外科实习。即使非常了解情况,第一次进手术室的我还是手足无措。我不知道该往哪儿站,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毫无征兆地,我就被猛然推进了这个紧张激烈的临床世界中。
众所周知,外科最糟糕的事是要耗费整个清晨和白天,还有许多关于外科医生多么刻薄的恐怖故事。尽管如此,首次轮科实习,我还是选择了外科。我非常确定自己不想做一名外科医生。所以假如在努力适应医院生活的过程中,我想犯犯傻,这正是机会。而且,假如我必须每天4点就起床,现在的天气也比较合适。
开始轮科实习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卡洛斯对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卡洛斯的轮科实习也是从外科开始的,只是跟我在不同的医院,他所在医院的工作繁重累人我们已略有耳闻。
“接下来这三个月中,你都别想见到他。他会像人间蒸发一样。”一个四年级学生警告我。
尽管我所在的医院工作节奏公认比较慢,但外科实习绝没有轻松可言。我和卡洛斯共同度过了二年级最后8个星期的每一天,我们一起准备资格考试,又一起度假。现在,我们开始担心长时间待在不同的医院里以及完全不同的值班时间安排会使我们无法见面。
星期一早上8点整,我走进了医院。外面晴朗而温暖,我却紧张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准备了一个小包,里面除了牙刷牙膏还有一套换洗内衣,应对万一晚上不能回家的情况。当我走进医院大厅的时候,看到一群同学已经等着去参加介绍会了。罗伊也在这里实习,不过他还没有到,他总是会迟到一会儿。
医院的候诊厅很小,靠窗的墙边摆放着两排棕色的椅子,窗外是医院的正门。木茶几将椅子隔成几组,每组2~4个椅子,看上去就像机场的候机厅。这家医院历史悠久,经过多年毫无规划的扩建,新老建筑掺杂在一起,成了一座复杂的迷宫。在医院待了三个月之后,我在从一幢楼走到另一幢楼时还是会迷路。
为期三个月的外科实习分为两个部分:两个月的住院病人诊疗和一个月的门诊实习。住院诊疗实习期间,我被安排到了外伤团队。这个团队除了负责普通外科之外,还负责抢救所有意外事故中的伤员。我还要在泌尿科、麻醉科和急诊室轮流实习。在门诊实习的一个月很轻松,我跟着整形外科医生和耳鼻喉科的医生正常上班。为了使自己的医院实践更充实,我还要到普通外科的门诊上实习,负责照顾那些有外科疾病的门诊病人。
普外科医生们要接诊许多肠道疾病患者,从梗阻、肿瘤到阑尾炎。他们还负责接诊肝脏和胆囊疾病患者、乳腺癌患者以及做甲状腺摘除和脾脏切除手术的病人。
7月1日,实习第一天,我还不清楚医院中的医疗组织构架,但我根据等级制度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住院病人依照不同的专科分派给不同的医疗团队进行治疗,每个团队由3~6名住院医生组成,他们要负责15~25位病人的治疗工作。每个团队由一位高级住院医生管理,他会记录所有病人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案,并协助团队中资历较浅的成员解决临床难题。刚毕业的住院医生被称为实习医生,在实习期的第一年中,他们在团队中肩负重任,他们负责接收新病人,并负责老病人的出院。医学院的学生们在这些住院实习医生的指导下工作,也渴望在少数病人身上能扮演和住院实习医生相似的角色。一位或几位已经完成住院医生实习的主治医生负责管理整个科室,确保我们不会犯错或疏忽潜在的问题,他们还负责给学生授课。这种组织构架作为一种核查和平衡体制,在给予毫无经验的临床医生独立工作、接受锻炼的机会的同时,也保证了病人的安全。每个专科都会以这种组织构架培训住院医生,并治疗病人。
在外科实习期间,我负责“接”病人,这意味着我要穿着无菌服走进手术室里——我要消毒,并穿上消过毒的手术衣,随后站在手术区域内观察手术过程。我还负责写术后用药和静脉输液时的医嘱;给病人作每日例行检查;监测他们的康复情况;记录化验结果;每天早上巡查病房时,向整个团队汇报病人的进展情况。我必须对各种治疗问题、手术过程和所有病人的术后并发症都胸有成竹。
对医学院的学生和刚毕业的住院实习医生们而言,每天的外科工作是从早晨5点至5点半的预查房开始的。在预查房时,我和住院实习医生共同收集病人的各种信息,以便掌握病人前一晚的情况。在正式查房前,我们得唤醒病人,给他们做体检,简要记录病情,写下每日的用药和静脉输液的医嘱。早晨6点,高级住院医生和初级住院医生会和我们一起正式查房。整个查房期间,高级住院医生、初级住院医生、住院实习医生会和我巡查每个病房,了解每一位住院病人的情况。我和住院实习医生要向高级住院医生汇报我们在预查房时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和问题,而高级住院医生需要一边记录这些情况,一边提供建议优化治疗方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住院医生查房后,我们还要进行简短的主治医生查房,在此期间,住院医生们要向外科医生汇报每个病人最新的病情进展。
最后,所有人都要进行手术前的准备。早上8点开始第一场手术,不过我们需要提前会见病人,使他们对手术有心理准备。手术时,会有一名住院医生做第一助手,协助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操作。医学院学生则收纱布,使外科医生的视野保持清晰还负责剪缝合好的线头。我觉得这两项工作都很单调。因为太矮我无法看清手术台上的状况,可是胆怯的我又不敢让忙碌的护士给我搬一个凳子。所以我经常会走神儿,听到有人喊:“剪断它!剪断它!”才察觉到真的有人正在对我说话。在缝合伤口时,我偶尔会帮忙。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负责观察流程并回答外科医生以及住院医生提出的所有问题,而且还常常出错。
我们通常会在手术室一直待到下午。做完最后一例手术后,住院医生和医学生重新碰头,做一个简短的晚点名查房。住院实习医生和我会总结每个病人一天的情况,值夜班的医生会记录下存在的问题和接下来12小时内可能发生的问题。查完病房后,其他的医生在处理好他们的病人之后,会在晚上下班时离开医院。值班医生整个晚上都要待在医院处理病人随时会出现的任何问题。
每三四天,我都会值一次夜班,而住院医生和住院实习医生的夜班更加频繁,每两三天就轮换一次。值班期间,我度过了各式各样的夜晚,从可以睡4个小时安稳觉的平静之夜到只能睡不到1小时的忙碌之夜。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可以承受如此严重的睡眠不足,不过还不像我想的那样糟。肾上腺素和咖啡因会帮我轻松度过一整天,实际上,难熬的是第二天。和住院实习医生不同的是,一旦我睡着了,脑子里就不再有任何责任感。我无须担心别人喊我名字。一般来说,学生还不足以重要到让病人费神寻找的地步。而住院实习医生却不得不时刻操心任何可能出现的麻烦,被别人喊醒也是家常便饭。
在介绍轮科实习和上临床教育课时,菲德曼院长曾经对我们说过:“你们不再是被关注的焦点,病人才是。”他在黑板上写下这句话,并在“病人”下面画了两条线,以示强调。这对我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闻。病人到医院是为治疗疾病,并不是为了当我的学习模型。学习教科书上病例的唯一目的,是让我们深入了解疾病的原理,而现在,真正的病人已经来到我们面前,等着接受真正的治疗。我不安的是临床老师也许会认为我会把学习当成关注的重点。
不过,在病房里,我很快就明白了,尽管对医疗团队来说是病人优先,但我的目标还是学习,医生们告诉我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我理应弄懂那些需要理解的事;提出那些我想知道的问题;完成那些我需要掌握的手术。一个住院实习医生还告诉我,有可能的话,无论我多么紧张或者觉得自己多么毫无把握,都千万不要拒绝千载难逢的手术机会。
斯蒂芬是我在急诊科(我在外科实习的第一阶段)遇到的首批病人之一。27岁的斯蒂芬面色苍白而憔悴,有亚麻色的平头和淡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很年轻。他自称有进行性尿频史,而且从上个月开始变得极为严重,并伴有极度口渴的症状,尽管食欲很好,但体重却减轻了不少。
尽管还不确定斯蒂芬所患的幼发型糖尿病(现在称为I型糖尿病)是何时开始的,但我敢肯定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护士用针戳了一下他的手指,将一滴血挤到血糖测试纸上,然后打开血糖测试仪。仪器发出嘟嘟的信号启动了30秒倒计时之后,开始分析血糖值。
“让血糖值升高吧,”我暗暗想着,“一定是糖尿病。”我希望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我随即意识到了自己盼望斯蒂芬患上糖尿病,这样我就会有一种满足感。这种念头使我愧疚不安。
血糖仪还在倒计时:5,4,3,2,1,嘟嘟嘟的三声信号之后,结果出来了。屏幕上显示“571”,这比正常的血糖值范围“70~130”高了太多。斯蒂芬有糖尿病,我的判断是对的。
我试图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来保持关注病人和学习两者间的平衡。尽管给斯蒂芬提供诊疗是首要的事,但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识别糖尿病的方法。
开始,我被医院的等级划分、工作节奏和责任义务给吓住了。虽然,在“病人-医生”第二阶段课程期间,我经历过包括外科在内的各种专科的小型实习,但医院对我来说似乎还是完全陌生的。现在,我那件穿了两年的白袍颜色有点旧,不再崭新挺括,而是皱巴巴的,我再次因感到周围都很陌生而无所适从。我不再背那个黑色的相机包了,因为那标志着我还是不属于病房的二年级学生,而我马上就是三年级的学生了,我把必须带的东西和参考书都塞进衣服的口袋里,白袍变得沉甸甸的。衣服口袋里东西的数量与穿衣者的受训水平成反比,识别出资深的住院医生和内科医生很容易,因为他们的白袍很轻薄。当你记住了更多参考书上的知识时,那些口袋里的手册就可以一本本扔开了。
在我沉重的白袍里面,还穿着手术服,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新的医生制服。这套衣服设计得绝对实用,它包括可两面穿的蓝色或绿色复合棉上衣和束带裤。而且还能让别人清楚地知道,着装者从事的是繁重棘手的工作。消毒服不分男女,但我即使穿最小号的,还是松松垮垮,很不舒服,我还要不时卷起裤腿以免绊倒。尽管如此,我还是为能穿上手术服而自豪,我渴望所有具体的证据,证实我的确是这个陌生的世界中的一员。
不同于一二年级和病人之间简短的互动关系,当我完全参与到病人的医疗管理和情感抗争中时,我与病人之间第一次出现了超过数天和数周的长期关系。随着时间的推进,我肩负起了越来越多的任务:给病人做诊断;向他们解释病情;制定治疗方案;进行简单手术。这些是我的病人,不再是那些勉强同意和我对话或者让我给他们做体检的姓名不详者。我还不确定这些医患关系将会给我带来什么,而且我吃惊地发现,前两年我遇到的那些主要问题在新的医患关系问题中仍占主导地位。在一二年级那些简短的会面中,每个病人只会引发一个问题。而随着医患关系的不断变深与加强,五花八门的问题开始混合交织进与每位患者的关系中。
二年级时,我很不习惯触摸病人这种亲密的行为,而且我面对病人赤裸的身体的时候还会不好意思。但三年级时,我对赤身裸体的病人已经习以为常了,丝毫没有侵犯别人隐私的感觉。我不仅开始触诊病人,而且又逾越了另一个界限,就是在做小手术的过程中,我会使他们感到疼痛难忍。一、二年级时,我第一次认识到了医患关系中双方的权利悬殊。不过当我学会向病人提出治疗方案建议时,我已经能面对这个问题了。前两年的“病人-医生”课程中,我曾遇到许多病危的病人,但我不用负责。可是现在,他们是我的病人,我对他们的死亡负有责任。
在医院工作期间,我对疾病和治疗逐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第一次可以真正地回答病人提出的一些医学问题。但由于对自己的临床水平一直抱怀疑态度,使我很难认识到这种技能上的提高。大多数时候,我仍然觉得,做一名真正的医生是遥不可及的事。
开始首次轮科实习的时候,我欣然发现自己喜欢待在医院里,并且喜欢成为医疗团队中的一员。尽管我非常喜欢在医院里照料病人,却不是特别喜欢外科。我的双脚还会因为在手术室长时间站立而隐隐作痛。尽管能理解这种紧张,但我还是很讨厌手术室里的气氛。除此之外,那些平时看似心平气和、温文尔雅的外科医生,一进手术室就成了另一个人,这也是我讨厌手术室的原因。一点儿事都会使他们把压力迁怒到其他同事身上。经过和同学们的多次讨论后,我们很快总结出了一个模式:外科医生会对替他传递物品的手术室护士大吼大叫;手术室护士会对替她传递物品的巡回护士大吼大叫;而巡回护士总是对正集中精力收取纱布并竭力想躲避这种呵斥的医学院学生们大吼大叫。一次大肠手术中,一位住院医生主刀,而一位资深外科医生在一边监督。资深外科医生一边看她切开皮肤,一边讲笑话。不过,有时他会对住院医生的技术很不满意。
“你在干什么?你打算把一切都搞砸吗!你不能这样做!”他一把夺过住院医生手上的手术刀,给她示范了正确的方式。过了一会儿,当手术继续时,外科医生又开始讲他的笑话了。
外科医生们还把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带到了每周讨论病人并发症(morbidity)和死亡率mortality的MM会议上。这种例会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场合来讨论并发症和死亡,目的是改进手术技术和调整设备的设置,避免出现任何可能的错误。但是外科医生们的态度常常很刻薄,有一次,一位外科医生谈论了某个病人在疝气修复术之后发生了伤口感染。这是一种常见的并发症,肥胖的病人身上更常会出现,不管手术多么小心谨慎,伤口还是有可能发生感染。这位细心的外科医生用了一种大家公认的网格修补法来加固病人的腹壁,防止肠组织再从此处漏出后引发疝气。“我从来没用过网格法,”组织会议的外科医生说,“这就是我的病人为什么没有发生伤口感染的原因。”
外科医生停顿了一会儿,问另一位医生:“西尔弗斯通医生,你做疝气修补术的时候用过网格法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用过网格法。” 西尔弗斯通医生回答道。
“那么,布莱克医生,你在做疝气修补术时使用过网格法吗?”
“从来没用过。” 布莱克医生说。
讲述这个病例的外科医生被弄得心烦意乱。报告结束时,他表示病人已经恢复健康了,而且情况还不错。
我为这位外科医生感到难过。后来我才知道,他刚当上外科医生不久。其实有更合适的方式让他了解网格修补术的副作用,没必要当众羞辱他。三个月中,我每周都会参加MM会议,更多会议的气氛还是友好和睦的。但是平静中总潜伏着这种挑衅,它常常出其不意地爆发,让我感到害怕。
我发现外科的问题让人觉得好奇,而且病人们也很有趣,我喜欢这样的实习。不过当为期三个月的外科实习结束时,我还是决定离开这儿,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一辈子都忍受这样的环境。
在进入外科实习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收到了资格考试的成绩单。繁忙的工作几乎让我忘了它。一天午餐的时候,有个同学告诉我,他早上收到了成绩单。听到这话,考试时的紧张不安刹那又涌上心头。漫长的中午之后,住院实习医生终于放我回去查邮件。毫无疑问,等待我的是一个不祥的黄色信封。打开信封,映入眼帘的是成绩单背面的橙色曲线,上面是每一科选择题的曲线分布图。我的每项得分看上去似乎都很靠后,远远不到及格。我颤抖着双手把成绩单翻过来,当看到顶部一长串的“合格”时,我松了一口气。我又翻了翻成绩单,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把曲线图看反了。我兴冲冲地赶回医院,为自己通过考试而欣喜若狂。
我安安稳稳地通过了考试,并带着这份新的自信回到了医院。我向自己证明,我已经掌握了前两年所学的知识,我已经准备好继续前行了,我要努力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