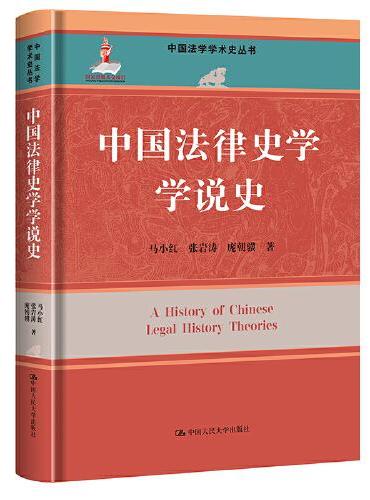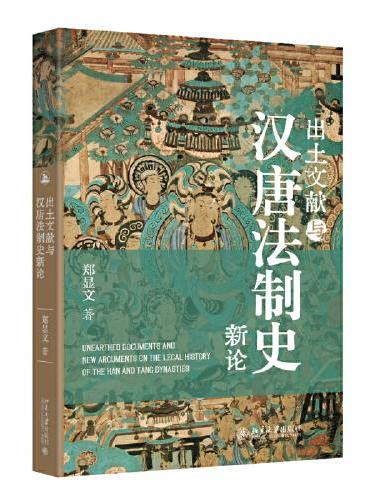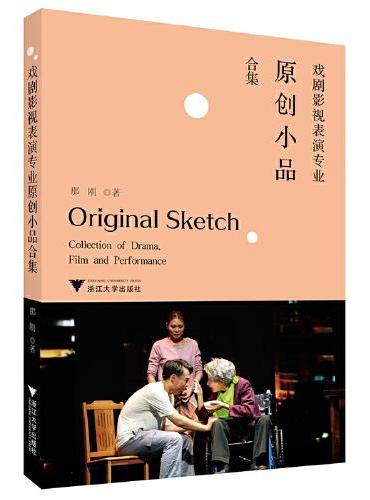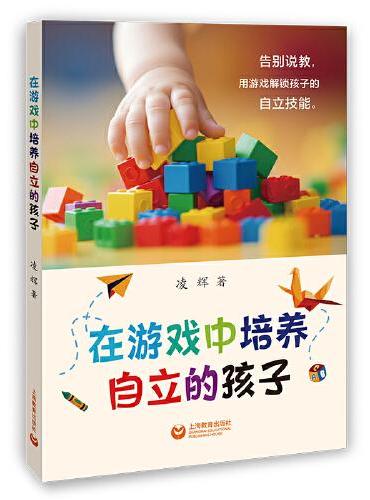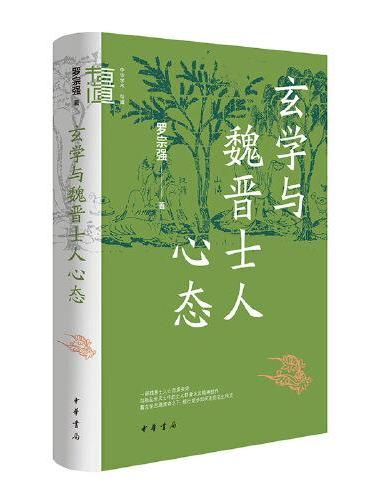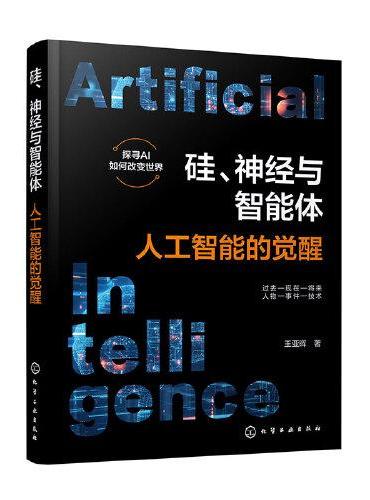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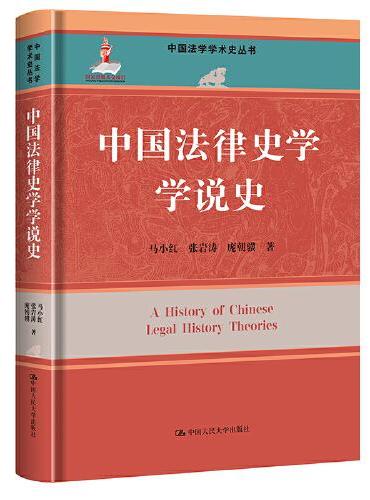
《
中国法律史学学说史(中国法学学术史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售價:HK$
184.8

《
方尖碑(全2册)
》
售價:HK$
1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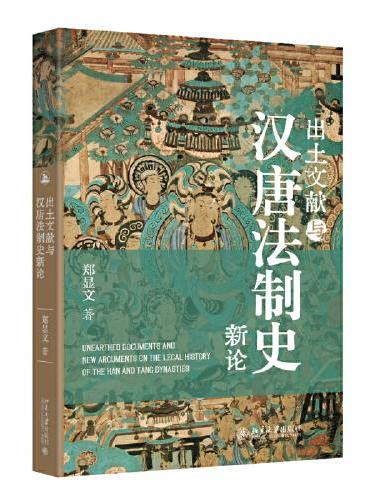
《
出土文献与汉唐法制史新论
》
售價:HK$
85.8

《
最美最美的博物书(全5册)
》
售價:HK$
1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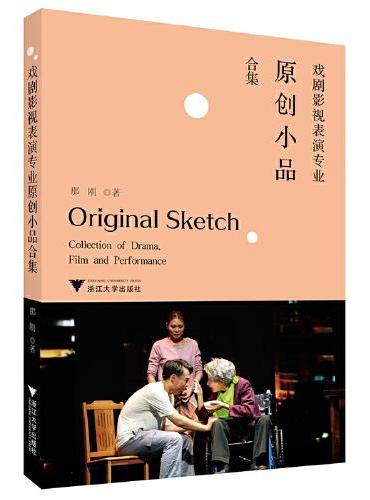
《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原创小品合集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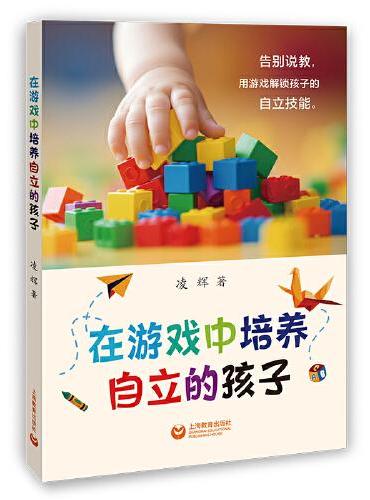
《
在游戏中培养自立的孩子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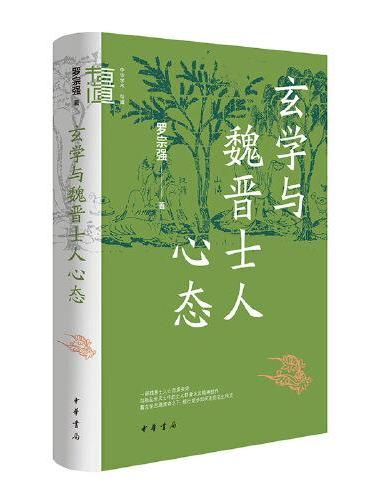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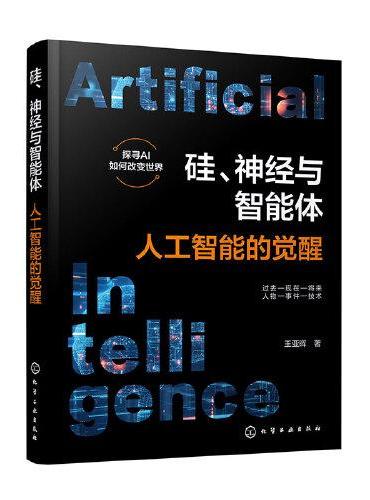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劳伦斯·布洛克是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最杰出代表,被誉为“纽约犯罪风景的行吟诗人”。他的作品引进国内的目前有三个系列:杀手凯勒系列、马修?斯卡德系列、雅贼系列,而“伊凡?谭纳系列”是引进作品中最后一个系列,也是他创作的最早的侦探推理小说系列。
《谭纳的非常泰冒险》是布洛克的“伊凡?谭纳系列”的第四部。伊凡?谭纳在这一部中不再是那个无论困难时多少,最后结局总是完美的人物,而是要直面真正的死亡,要面对死神在耳边猖狂地啸叫。面对这些,谭纳又将如何完成那些常人不可想象的任务。真相就在翻开书的那刻,向你展开。
|
| 內容簡介: |
伊凡?谭纳是世界各地隐秘组织的积极拥护者。朝鲜战争中的碎弹片让闹钟成了他最用不着的玩意——睡眠中枢被破坏,根本不用睡觉。
为了拯救深陷泰北丛林的女友,谭纳打了各种预防针,风尘仆仆从纽约,一路赶到泰北原始森林。身无分文、语言不通,被剥个精光后,关进鸟笼般的牢笼里,好不容易逃离即将被砍头的命运。
但谭纳仍不改初衷,决定继续深入原始丛林,寻找生死未卜的女友,只是他越深入蛮荒,越是疑云重重、敌友难辨。要如何才能杀出重围,救出女友呢?
|
| 關於作者: |
劳伦斯·布洛克 Lawrence Block
生于纽约州水牛城,现居纽约。
他是享誉世界的美国侦探小说大师,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备受推崇,还跨越大西洋,完全征服了自诩为侦探小说故乡的欧洲。
1994年爱伦坡终身大师奖得主,曾三捧爱伦坡奖,两夺马耳他之鹰奖、四获夏姆斯奖等重要硬汉派侦探小说奖项,2004年最终获得钻石匕首奖。
卜洛克目前著有五十多本长篇以及多部短篇小说。“伊凡?谭纳系列”是内地引进劳伦斯?布洛克“系列小说”的收官之作。
|
| 內容試閱:
|
这实在称不上囚笼,别用常识揣度。一般来说,所谓的囚笼,指的是某种建筑物里的某种房间款式,通常有加了铁柱的窗户,地板要么石头,要么水泥,一张烂床,头顶上一盏要亮不亮的灯泡,室不雅,也不大,但是,人体的各种功能,基本上,还能舒展。
我在伊斯坦布尔,就住过这种牢房。我不怎么欣赏,但好歹原汁原味,中规中矩。
可不比我现在待着的这个。不知道哪个白痴设计的,偏偏把我给关了进来。这笼子八英尺见方,四英尺高,全由竹子搭成,悬在一根粗树干上,离地五英尺。
这哪叫囚笼?如果你是见到什么东西,都觉得它该有个名字的那种人,那么,管它叫大鸟笼吧,而且还是方圆数英里之间,唯一可以见到的大鸟笼。泰国北部,柚木林浓荫蔽天,鸟儿自由自在,是个天然的大鸟园。这里的鸟,种类不少,花色斑斓,体态轻盈,可惜叫声有些刺耳,绝对受不了鸟笼的拘束。
我也是。
四天前,我被巡逻的游击队逮住,就一直窝在这个笼子里。实在不敢相信,搞了这么久,才过四天,只是感官认知提供的证据,不容狡辩:日头升落四次,总得把太阳当回事吧。
我已经熬不下去了,关在里面,度日如年,可能就是这个囚笼原始设计的目的,让里面的人,尝尝东方酷刑的厉害,站不起来、躺不下去,勉强有些空间爬一下,却万万爬不得。正中央掉着一根绳子,是囚笼跟树上唯一的联结。换句话说,只要稍微移动一下,囚笼立刻会倾斜到一边,顿时失控,里面的人一定会狠狠一摔,问题只是跌在地上,还是撞上树干。
就算境遇没这么惨,说真的,里面的人也没有理由从这一头,移到另一头,干什么呢?那一头跟这一头还不是一样?我想尽办法,挣扎出不同的姿势,勉强从竹子的缝隙里面,打量这个游击队基地。我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大概拼凑出外界的长相:几幢茅草屋、几堆炊火、几支步枪、几把大刀、整排削尖的竹子,还有一群泰国游击队,甚至还瞄到了我的衣服套在几个游击队员的身上,在囚笼里的我,裸着身子,像一只拔光羽毛的鸟。此外,就没有什么值得我甘冒被震得七荤八素的风险,离开平衡点去窥探的重点了。
在囚笼地板中心,有一个小洞,切割得还算爽利。如果外面的人记得的话,一天会送两次饭来,不过,他们偶尔也会忘记笼子里面还有人。三不五时,不知道谁会从洞里,递一碗油油腻腻的水给我。该排泄的时候,这个小洞,也是我抒发的管道。可能会有人以为入口的食物、饮水没多少,出来的东西,想来也多不到哪儿去。但显然,送进来的馊米饭、脏脏的饮水,或是两者携手合作,让阿米巴得以大显身手,害我罹患了严重的阿米巴原虫腹泻。第三天中午,我开始担心,吃没多少,却拉了一堆,迟早会拉得见不到人影;或者,整个人拉得翻了过来。第四天,肚子好了,我又担心会饿死。
我直不起身子,没法走动,不能休息,饮食恶劣。我在囚笼里寻了个地点,把重心放在臀部,先伸直我的背、我的脚,再盘成一个瑜伽莲花的姿势。我越来越热,越来越饿,越来越无聊,随着时间的消逝,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刚开始,我害怕他们会杀我,现在,我却担心他们不杀我。
如果我睡得着的话,情况就不会这么糟了。但我十八岁那年,一枚北朝鲜的榴弹片,不偏不倚地嵌进我的脑子,摧毁了一个被称作是“睡眠中枢”的地方。截至目前,医学还搞不大清楚到底什么是“睡眠中枢”、有什么功能,但它故障了,之后的十七年,我从来没睡着过。
还好的是,睡不着也有睡不着的好处:除了每个月帮我挣一张一百一十二元的政府残障支票之外,也让我有更多清醒的时间,料理身边的各种事情。旅行,用不着睡旅馆,生命,因此变得更精彩。
睡眠,除了麦克白形容的苦役后的沐浴、受创心灵的油膏、生命每天轮回一次的生死之外,在无穷无尽的无聊折磨中,睡眠更是打发时间的利器、困境中的一大解脱。照理来说,我这趟行程,深入丛林,早就该筋疲力尽了,要不是在我脑子里那片榴霰弹的碎片,窝在囚笼里一半的时间,我肯定会幸福得昏厥过去。
然而,我却始终醒着。
我还真没这么闲过。第一天,我制造噪音,吸引他们的注意,先用流利的泰国话,再用不怎么地道的柬埔寨语,大吼大叫。他们压根懒得应我几句,倒是有人走过来,把囚笼一举,我二话没说,在笼里狠狠地跌了个狗吃屎。自此之后,只要我有个风吹草动,也不管我用哪种音调、哪种语言、什么内容,就有人来这么整我一下。我学乖了,闷声求平安。
没人找我讲话。我的沉默换来相同的沉默,连拷问都没有。刚开始,我想跟他们解释,我,伊凡?麦可?谭纳,不是美国情报人员;后来我想跟他们说,我,伊凡?麦可?谭纳,的的确确是美国情报人员。只是我盘算的两套说词,完全派不上用场。没有人问我任何事情,根本懒得管我叫什么名字、兵籍号码几号,真的,完全不鸟我。我只得窝在这里,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等什么。老天爷显灵吧,也许。一道霹雳打在树枝上,囚笼应声跌下,摔个粉碎。要不,就是营地遭到忠于国王陛下的政府军奇袭,美国陆战队、美国骑兵队也成。绝大部分时间,我强迫自己不要想我到底在等什么。我在囚笼里没事干,找不到方法挣脱出去,即便是离开了这个劳什子,我也不晓得往哪逃。等待的最后结果就是继续等待,其实,我根本什么也不用等。
在一个暮色深沉的傍晚,终于有人跟我说话了。一只手,把一碗米饭,从囚笼中央的小洞塞了进来。我贪婪地一把攫住那个饭碗——他们早上没给我饭吃,不知道是一时粗心,还是刻意整我。我狼吞虎咽地把这碗饭、里面的虫子,全部塞进肚里。这话讲来轻松,实则恶心至极。但你只要吞过一两碗这样的东西,就不会觉得虫子在你的胃里不住蠕动了。蛋白质,毕竟,还是蛋白质。我把空碗交出去,换得一杯温水,喝了水,还了杯子,听得一个温和的声音说:“明天。”
也许他说的是“早上”。泰国话跟许多语言一样,“明天”跟“早上”两个概念,是混在一起的。我的朋友,到底是泛泛地说“明天”,还是专指“明天早上”,单单这么一个字,实在很难判断。
于是,我重复了他的话,“明天”?“早上”?不管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应该都照顾到了。
“日出的时候。”好了,这样清楚了。
“日出的时候要怎样?”
“就在日出的时候,”他的声音有点哀伤,“他们要杀你。”
这句话让我重燃希望。
让我在这里补几句话,我突然振奋起来,并不是因为他告诉我一个事实:明天一早,我就可以告别囚笼里的悲惨生活,撒手人寰。尽管窝在这个囚笼里,难过得要死,但是,真的去死,好像也不是比较好的选择。我的希望并不是来自于他告诉我的讯息,而是他说话的观点。换句话说,重点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请听好:“我们要杀你”跟“他们要杀你”这两句话的差别。“他们要杀你”意味他个人不在局内,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他并不愿意卷入这场血腥杀戮。他的声音强调了这一点——他们要杀我了,他觉得很难过。而且感觉起来,他是违背了组织的规定,私底下向我透露这个机密的消息。
“他们会在日出的时候杀掉你。”他又说了一遍。
此时,我正摆出一个瑜伽的莲花姿势,大腿交叠,朝天的脚掌,交错搁在另外一腿的膝盖上。我解开双脚打成的结,伸直身体,翻身朝下,嘴挨近囚笼下方的洞口。囚笼有些倾斜,我尽可能地保持笼子平衡,但是,内心激动,却是澎湃汹涌。在晨曦中,我可以清楚看到向我通风报信的线民:快二十岁了,瘦瘦高高的,一头短短的头发,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娃娃脸,在这个地方称得上是异数了。
“他们在商量,是不是给你找个女人。”他的声音还是有点哀伤,“男人在上断头台前,一定要找个女人睡一次,这是规矩。最早以前,这是帮那些没有孩子的男人,设法留个种;可是有人说,谁知道要处死的人有没有孩子呢?所以,干脆,每个死囚在死前一夜,都帮他安排一个女人算了。”
死到临头,的确有人会性欲勃发。但此时,我没有半点要发泄的意思。即便是一顿好吃的断头饭,或是一杯香醇的威士忌,也勾不起我的兴致。我只想逃出这个囚笼。
“但是,”他又说了,“这次他们不会给你准备女人,因为你是白鬼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不能玷污我们纯洁的血统。他们已经决定了。”
又是他们。我正想表达我的感激,谢谢他偷偷告诉我这么好的消息,但他显然没有心情接受我的恭维,他有更难以启齿的烦恼;而我,正竖起耳朵,全神贯注,生怕漏了一个字。
“我没有过女人。”他说。
“从来没有?”
“我这辈子,还没睡过女人,我老是挂念着她们。”
“这是人之常情啊。”
“我常常看着她们。”他的声音有些梦幻,“看她们走路的样子,你知道吗?她们的身体、大腿、微微侧着的俏丽脸庞,还有她们银铃般的声音。我满脑子都是女人。”他突然陷入了漫长的沉默,或许又开始想女人了吧。他有一对棕色的大眼睛,前额挂了一串汗珠。“天天,天天……”他突然说道,“脑里一片空白,就只有女人……”
“你从来没有过女人?”
“从来没有。”
我突然觉得我很像《花花公子》的性心理顾问。“那你……为什么不,呃……去找一个呢?”
“要怎么找?”
“这个嘛……”
“女人不喜欢我。”他说,“我一靠近她们,就变得很紧张,满手是汗,喉咙又干得要命,舌头像一只蹦出岸边、眼看就要没命的鱼,半个字都说不出来。我的膝盖软得撑不住我,世界天旋地转……”
看来他还真有问题。要不是在这小命即将不保的环境里,我或许会更同情他一些。可我自己也有问题啊,而且命在旦夕,可没时间像他这般从容地多愁善感。没睡过女人,一时半刻还不会害他丢掉性命,可我再窝在这个囚笼,明天不是被吊死,就是被砍头,要不就得面对他们更有创意的杀戮手段。
“我想你有过女人吧。”
“喔,”我说,“有,我有过女人。”就是因为我有了个女人,一个叫做图潘丝?努嘉瓦的女人,才害我跑到泰国这个鬼地方。
“你有过很多女人吗?”
“也没有很多啦。”
“她们是怎么个模样?”
“比火腿好些。”
“你说什么?”
“没事,胡说两句。”我说。这是一个关于拉比与牧师的老笑话,泰国人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个典故。而且,再怎么样,也只是句闲话,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赶紧逃命,我唯一的希望,当然,就是这个苦闷的处男——
当然。
“这世上找不到比抱着女人更过销魂的事情了。”我说,“在这方面,我的经验可丰富了,跟你保证,欲仙欲死,无与伦比。软软的,甜甜的,女人的身体、胸部、饥渴的嘴唇,温柔、小鹿般的眼睛,女人的味道,若有似无,让你血脉贲张……”
我顺着这个理路,继续加温,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可怜的小丑,刚开始还有点莫名其妙,现在,他的情绪已经被我激到愤怒的边缘。“够了。”他终于说话了,“别再说了。”
“你怎么可能没享受过这种人生乐趣呢?如果我在外面,就能帮你想想办法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