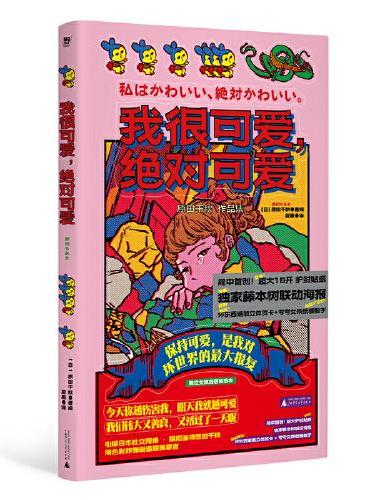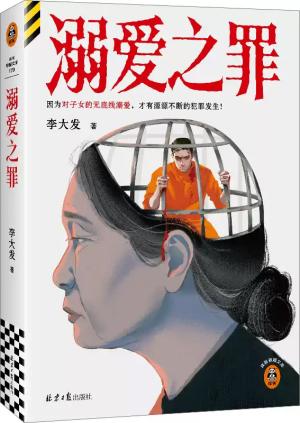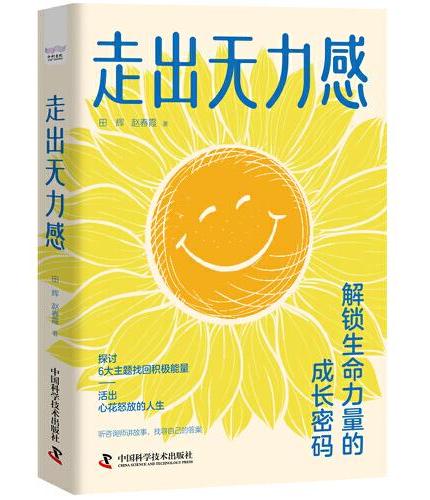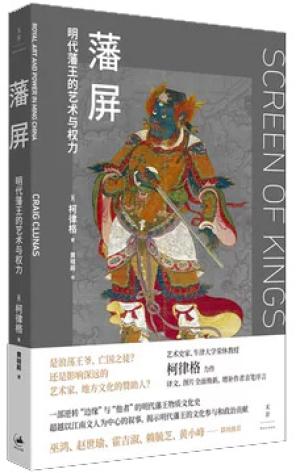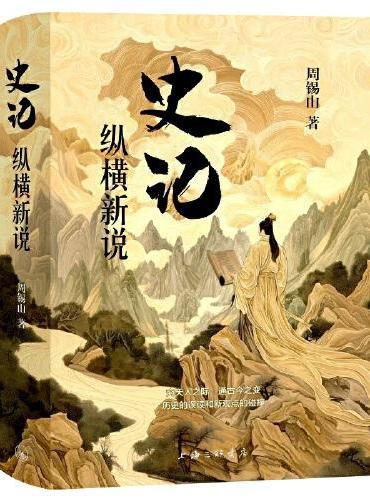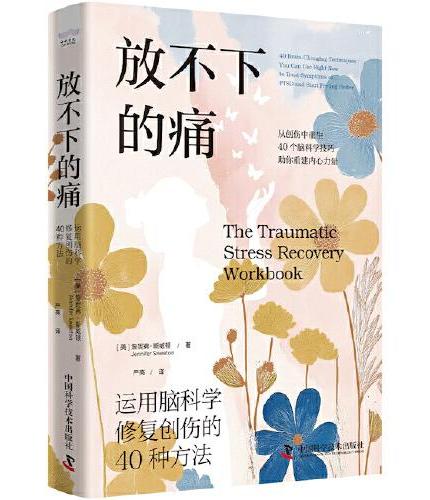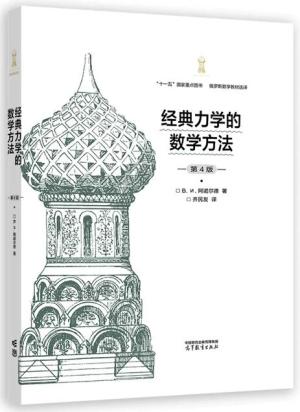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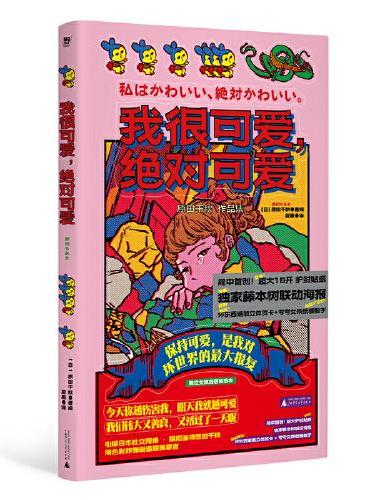
《
我很可爱,绝对可爱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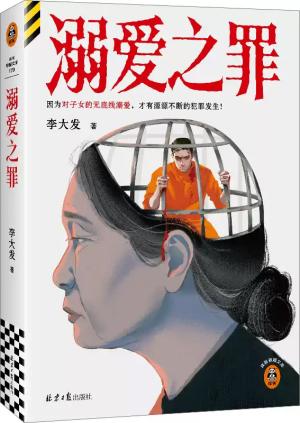
《
溺爱之罪
》
售價:HK$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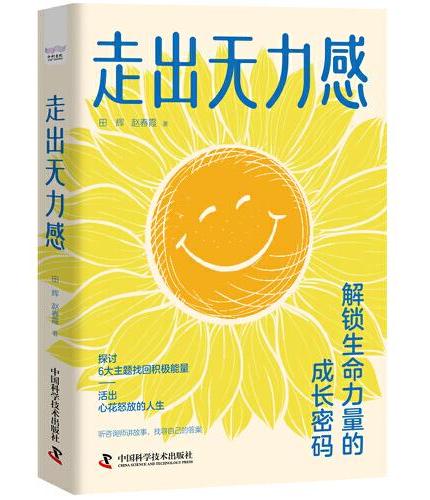
《
走出无力感 : 解锁生命力量的成长密码(跟随心理咨询师找回积极能量!)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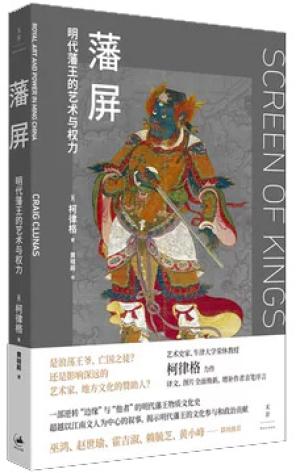
《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柯律格代表作,一部逆转“边缘”与“他者”的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填补研究空白)
》
售價:HK$
1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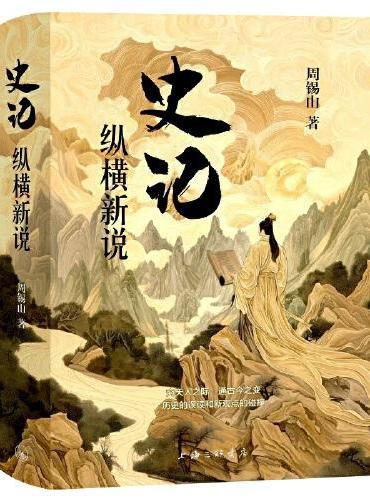
《
《史记》纵横新说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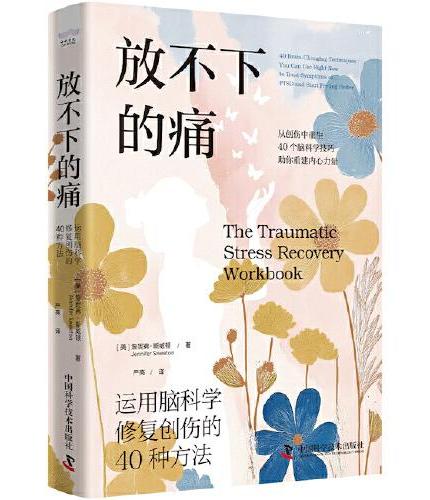
《
放不下的痛:运用脑科学修复创伤的40种方法(神经科学专家带你深入了解创伤背后的脑机制,开启全面康复之旅!)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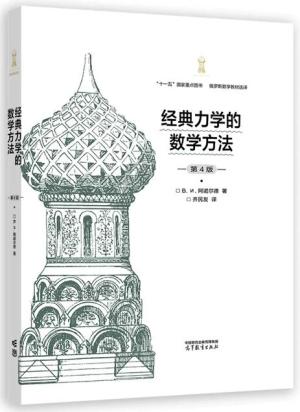
《
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第4版)
》
售價:HK$
86.9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跟随历史的足迹 见证一个民族的觉醒与抗争
》
售價:HK$
65.8
|
| 內容簡介: |
|
一部“观念史”的著作,探讨了自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学诞生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客观性”这一神圣理想和核心规范所遭遇的命运,即其形成和衍变,受到的挑战和修正,如何得到捍卫,以及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观念的风起云涌,终于不可遏止地走向混乱和解体。
|
| 目錄:
|
前言
导论 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篇 客观性的加冕
第一章 欧洲的遗产:兰克,培根和福楼拜
第二章 职业化的计划
第三章 共识和合法性
第四章 最优雅的反叛
第二篇 受围困的客观性
第五章 历史学家在后方
第六章 风云突变
第七章 职业化的停顿
第八章 分歧和反叛
第九章 交战
第三篇 客观性的重建
第十章 为西方辩护
第十一章 趋同的文化
第十二章 自主的职业
第四篇 客观性在危机中
第十三章 分崩离析
第十四章 每个人群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第十五章 中央失守
第十六章 以色列无国王
附录 本书引用的手稿集
索引
出版后记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欧洲的遗产:兰克,培根和福楼拜
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了。到这一年,美国的对外贸易进入顺差: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0亿美元。到世纪之交,对外贸易的顺差扩大到50亿美元,美国出口的棉花、小麦、机械和其他产品源源流向国外。但在那些年代以及未来的—段时间里,从思想上讲,美国依然是个进口国。
美国历史学家建立了职业规范体系,特别是客观性这一核心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吸收了欧洲的大量思潮,其中必然首先要借鉴德国的历史学学术规范。“科学方法”也属于此类。在那个时代,科学性意味着现代性和权威性。他们选择了德国的严谨学风。正是这种学风把职业历史著作与业余历史学家文辞浮华的著作明显地区别开来,职业历史学家也在试图取代业余历史学家的地位。
美国历史学家依据他们对这些思潮的理解,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往往是依据错误的理解,确立了职业化史学思想的基础,并且在美国形成了一种意识。
1
布利斯·佩里(Bliss Perry)写道:“德国人拥有学术的独有秘密,对此,我们18世纪的那些年轻人从不怀疑。1814年,当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和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在波士顿登上客轮,驶向哥廷根大学去求学时,对此更加坚信不疑。”整个19世纪,留学德国的美国年轻人有成千上万,他们到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以及德国其他大学和学术中心去接受专业和学术的高级训练,因为直到那个世纪末,美国还没有形成这种方式的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英国大学所关心的问题是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学者。1871年以前,凡是向英国大学申请学位的人必须先在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上签字。在法国,要取得大学的高级学位相当困难,如果要在索邦大学从事冥思苦想的学习,在法国的首都有可能遇到吃“臭肉”的危险。这些人还必须准备让他们的灵魂勇敢地面对“无神论”和“教皇论”的双重危险。此外,在德国求学花费不那么昂贵。在19世纪80年代末,留学生一年的花费,包括交通费用,估计比在美国著名大学学习一年的费用少三分之一。
许多年轻的美国留学生在德国学习历史学。他们发现,那里的高等教育机构,无论从它的结构还是从它的价值观念来看,都与他们原先在国内了解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在美国上大学时,学校依然以道德理论的教育为主,向他们灌输精神的、行为的和宗教的“纪律”。学生的生活安排非常紧凑,有严格的和强制性的校规。教室里上的课程大部分属于机械的重复。创造性的思想被视为对新教虔诚的威胁。他们在德国看到的大学模式引发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场革命。一批新型的大学,如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克拉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相继创立,一些比较古老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执根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也得到了改造。按照德国人的观念,“真正”的大学应当是探索者组成的共同体,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培养新一代的学者(Gelehrten),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是严谨的学术风格,而不是宗教和哲学的正统观念。
美国留学生在德国还看到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典范,强调个人的作用。那里的大学教授(Herr Professor)就属于这类典范。德国的教授与他们在美国看到的教授判若两种人。美国教授衣衫褴褛,像一种可笑的人物。德国教授却非常富裕,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普鲁士大学的正教授平均工资达到1.2万马克,是小学教员工资的九倍,而小学教师在德国经济地位的阶梯上远非处于底层。最有声望的大学教师年薪甚至可以超过4万马克。成功的大学教授在德国社会地位系统中接近于部长。在那里的社会中,最受尊重的人往往不是贵族。教授们虽然没有贵族头衔,但受到了社会的最高尊敬,即使是女教授(Frau Professor)也受到社会的极大尊重。
这些美国研究生在他们的德国导师领导的历史学研究班(histcrrische Vorseminarien)里看到了搜集和考证史实的各种各样高超而深奥的技术,例如古文书学、古钱币学、古铭文学和金石学,等等。这些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中的严谨性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史实进行辛勤和艰苦搜寻的工作能力。他们的理想是做—个“到大海里捞针的人”(原文是做—个“跨越重洋去验证—个逗号”的人。——译者注)。
仅仅依靠职业动机还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艰苦努力。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说道,探索知识的人与“粗俗的从业人士”完全不同。他们是社会中“仅存”的圣徒。他们对知识的执著热爱“绝对不会受到不良动机的玷污”。G.斯丹利·霍尔(G.Stanley Hall)曾经说过,一颗爱好探索的心灵“需要完全放弃自我”,研究者是“追求真理的圣灵骑士”。理想的研究生“必须具有天赋,心中藏有天火”。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最充分地体现出了德国那种“执著追求历史真相”的神圣理想,而且正是这种理想给予了他们生存的动机。赫伯特·列维·奥斯古德(Herbert Levi Osgood)的女婿迪克森·瑞安·福克斯(DixonRyan Fox)是这样说他的:“只要看见他在工作,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种虔诚的意志在驱使着一个赢弱的身体,完全超过了他的精力极限。他全心全意地投入研究工作,就像修道士那样忘乎所以。”哈佛大学的中世纪史学家查尔斯·格罗斯(Charles Gross)工作时也是全神贯注。他的同事说,“他工作时精力非常集中,达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他不停地咬着手指甲。他在剑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有时连吃饭都忘了,即使吃饭也很不定时。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原因让他患上了致命的疾病。”
他们把在德国大学里的学术经历以及对这种经历的看法在美国复制了一遍。在堪萨斯和肯塔基,想成为德国教授那样受人尊敬的人变成了他们的梦想,只要把学术看作是一种技术性的、专门化的和严谨的探索活动,理所当然地就能获得神圣的职业,所有这些观念都以多少可以识别的形式带回了美国,而正是这些观念在美国历史学家意识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我们从制度、社会、技术和道德等方面转向明确的哲学和认识论方面,德国的现实与美国的观念之间存在的差距便显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要理解美国特有的正统究竟是什么,就必须对这种差距进行探讨。
爱德华·A.罗斯(Edward A.Ross)19世纪80年代曾在柏林大学留学。当他谈到这段经历时说,那里的“基调”是,“科学的客观性(wissenschaftliche Objektivftiit)是最庄重的词语”。这里需要考察一下他所说的那个“基调”如何在美国复制。这一点很重要。在德语中,Wissenschaft一词应当如何翻译?从外延上看,按照德语的用法,它带上不定冠词(eine Wissenschaft)有“一门科学”的意思,是指有组织的信息体。而学者们收集和解释信息的集体活动则应带上定冠词(die Wissenschaft),指的是“科学”。带定冠词的“科学”相当于英文里的“学识”(scholarship)或“学问”(learn—ing),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相应于英文中的“科学”(science),因此在德语中带不定冠词的“科学”实际上指的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正如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所说的,“在英语中根本不可能讨论社会学和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但在德语中,历史学被定义为一门科学。如果有人问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意味着对社会学是不是一门具有独特的和特定范围的学科地位表示怀疑,而不是说它是否带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个词的内涵是根源于理念主义的哲学传统并从中发展出来的。“科学”指的是献身的和神圣的探索。它指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是自我实现。它所指的不是实际知识,而是有关终极意义的知识。如果说“科学”一词带有理念主义的含糊意思的话,那么对于常用的“人文学科”(Geisteswfsseschaften)一词中含有理念主义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但这个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是指“精神研究”。历史学像哲学、文学或神学一样,无疑是一门“人文学科”。有人提议可以将自然科学的(naturwissenschaftlich)研究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的领域,对这样的建议德国历史学家做出的反应是表示愤怒。
19世纪美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其中曾经在德国留学过的大部分人,真的以为wfssenschaft一词可以当然地翻译为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吗?他们真的相信科学的历史研究意味着采用自然科学中(所谓的)纯经验主义的和价值观中立的方法吗?这种说法完全缺乏想象力。但是,我们在下面很快就会看到,大量的事实证明,大多数历史学家确实有这一类的想法。
……
|
|